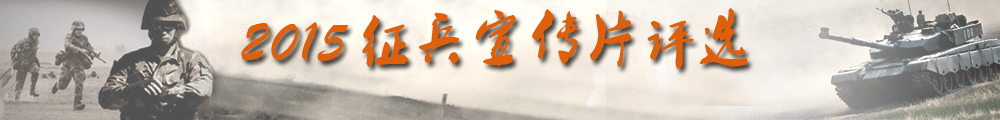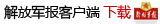编者的话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纪念和回顾70年前的那场民族自救斗争,必须将其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视野中去分析和思考。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西南重读丁玲和肖洛霍夫两人的二战题材小说作品,把两个民族、两个战场、两个作家及其作品对照、比较,进而对抗战文学的价值意义、评价标准进行了反思。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叙事(六)
不能忘却的仇恨与使命
■张西南
丁玲和肖洛霍夫笔下的战争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战争最残酷、最激烈、最艰苦的岁月里写下的文字却永远留给了后人。尤其是在今天,仍能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面对那些不惧流血牺牲站立在斗争最前沿的前辈作家,我们应从他们身上感悟并传承什么,这或许是文学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最需要做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丁玲(左)肖洛霍夫(右)
1939年春,年仅34岁的丁玲在奔赴延安两年多,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敌后,创作出了短篇小说《新的信念》。
或许在丁玲的文学大厦里,这部旧作并不显赫甚至有些单薄。但是,当我们翻开早已发黄的书卷,还能从中闻到混合着血腥和硝烟的味道,“我们不是为了给鬼子欺侮才活着的呀!”“只要你们活着,把鬼子赶跑,大家享福,我就死个把儿子也上算。他虽然死了,我会记得他的,你们也会记得他的,他是为了大家呀!”这就是丁玲笔下的母亲发出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仍振聋发聩。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温丁玲旧作,不仅仅是为了纪念70年前的那场伟大胜利,更重要的是不能忘却我们民族遭受的苦难,不能忘却拒不认罪的刽子手们欠下的血债,不能忘记老一辈文学家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作枪的崇高风范,这就是温故知新的意义所在。
丁玲:“到前线去”
丁玲的抗战文学之旅,是从“到前线去”开始的。时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的她,迎着西北风,攀爬陡峭的山路,每天都是80里、90里的行军,采访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左权以及普通的战斗员,写出了第一部抗战题材的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此时临近抗战全面爆发,也是丁玲抗战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从化险为夷的“冀村之夜”,到“临汾”与129师相遇;又从牺盟会的“马辉”,到“致孩子剧团”,不久再赴前线,到晋察冀边区去,直到“七七”事变周年之后,应该是丁玲抗战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年月,丁玲回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在鲁艺、在解放日报、在霞村,写出了受屈辱的贞贞、入伍的杨明才、在医院中的陆萍、夜里的农民夫妻,《新的信念》就在此时问世,属于丁玲抗战文学第三阶段的作品。随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丁玲经常出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我们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对边区的老百姓和英雄模范以至三教九流,身心都贴得更近,熟悉了解也更全面透彻,不仅写出“十八个”决死的官兵,“二十把板斧”的传奇,还全景式描绘了“129师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战斗风貌,同时勾勒出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的侧影、麻塔村的群像、骡马大会的繁荣,构成了一幅“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烟图”,也可以看作是“劳苦大众的风情画”,为丁玲抗战文学之旅的最后阶段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简约叙述丁玲的抗战经历,既对作家在此期间的文学实践和创作成就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也是为了加深认识一个毕生追求进步和光明的女性作家,在烽火年代走过的艰辛征途和她复杂的心路历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重读《新的信念》,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作家所表现的“信念”是什么,新旧差异在哪里,其价值和意义又该如何认识,以及对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新的启示。
《新的信念》所讲的故事发生在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山西狼烟四起的危亡之日。作家一方面看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另一方面也看到了“有的自卫队员白天村里开了欢送会,夜晚又偷着回家”,“那些女人的声音,分不清是号叫还是哭泣,紧缩的恐怖之感压到身上来”。后者,在1946年4月召开的“抗战八年文艺检讨”座谈会上,艾芜的发言给予了证实。他说,“我觉得在大后方的农村里有两种农民:第一种农民是被残酷的压迫着,在饥饿、贫困、痛苦的深渊里,听天由命地生活着。第二种农民是比较觉悟的,他们憧憬人民的武力,希望改变他们的生活。对于当兵的态度他们是有条件的,如果是官兵待遇一律,他们当兵,否则怎样强制也不行。”其实,这种现象在前方、在城市、在不同阶层的人群中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教育动员包括农民在内的大众觉醒和奋起,不当亡国奴,拼死在疆场,已成为抗战初期最突出、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丁玲到延安以后对此有了切身的感悟,“我不能自已要把这些记录下来”,“和人民共忧患,同命运,共沉浮,同存亡”。于是一位惨遭日本兵强暴而死里逃生的“老太婆”成为了丁玲笔下的主人公。“拖着蓬乱的几缕头发,投过来空洞呆呆的眼珠”,“望着那老去的脸,像一块烂木头,嵌着鱼一样的眼睛”。在那个年月,这是千千万万个受侵略者欺侮迫害、忍辱负重的母亲形象。但丁玲没有去写“老太婆”的悲戚,而是主要写她“求生的力”,写她大难不死的觉醒,写她用愤怒和仇恨“煽起的火焰”。
开始,“老太婆”在家里讲述孙女遭鬼子强暴后被喂了狗,孙子又被鬼子的刺刀挑了,咆哮着训斥只知道叹息和流泪的家人,“你们哭吧,你们只有这些不值钱的尿,你们等着吧,日本鬼子还要来的呀!”儿子的仇恨燃烧起来了,“我要用日本鬼子的血,洗干净我们的土地!”接着又给邻居们讲,“那些他们所关心的父母老婆儿女是怎样牺牲在屠刀下,又是怎样活着,受那没完的罪”。丁玲用她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老太婆”从觉得羞耻、痛苦而不能说下去,到觉得她的仇恨也在别人身上生长而忘了畏葸,再到懂得什么辞句更能激动人心,一层一层地展示了“新的信念”在她干枯而不屈的心田里扎下根来,并经血泪的浇灌发芽生长。
随后,“老太婆”满村子巡视,指着那些遭劫的地方厉声问着“你们会忘记吗”,要是街上人少,她就闯到别人家里去讲,一点眼泪也没有。参加游击队的儿子回来后,她没有诉苦而是对他说,现在是枪杆子的世界,她喜欢听那些打鬼子的故事。“老太婆”把这些故事到处倾述,当又看见眼泪,又看见一些人“心中所起的战抖”,她就会去“抚摸那些受了伤的灵魂”,动员“大家都上队伍去”,如果有人迟疑,她就吼起来“你这孱头,你怕死!好!你等着日本鬼子来宰你吧,我看见宰这像烂棉花一样的人呢”。在“老太婆”声情并茂地鼓动下,许多人上队伍去了。
此时的“老太婆”,已不再是那个被欺辱的痛苦形象,而已成为一个觉悟了的有救亡胸怀的抗敌战士。她带着两个儿媳妇和惟一的孙女一起加入妇女会,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游击队或农会,她所带领的不再是一个家,而是全村的妇女,还动员了好几个村子的群众,汇聚成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泪的传统母亲的形象,一个饱经磨难而不屈不挠的革命女性的形象就这样重叠在一起,成为有着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典型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英雄母亲的形象。
对于包括丁玲在内的投身抗日前线的作家作品如何评价,人们的认识从来就不尽相同,以至今天仍难形成共识。早在抗战期间,文艺界就有一种论调,认为抗战时期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是空洞的,甚至讥讽嘲笑到前线或其他地方去搜集创作素材的作家、艺术家,并给一些动员民众坚持抗战,鼓舞民众上山打游击的作品戴上“抗战八股”的帽子。这在当时就受到了一些作家的反对,艾芜明确表示,“作家能长期实践生活斗争,自然再好不过,并且希望能这样做,但因种种关系,作一短时期的搜集材料工作,也用不着加以嘲笑的。”阳翰笙也说过,“我就曾经亲眼看到过许多士兵看了所谓‘抗战八股’的戏,曾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来的事实。”包括曾经沉浸于唯美的梦幻中的何其芳,在抗战胜利前夕也非常客观地评价:“延安那边的艺术工作,有着过去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抗战初期又在鼓舞抗日情绪,提高胜利信心上有了相当大的成绩,而且艺术工作者们在主观上可以说都是想以艺术来服务人民解放的事业的。”刘白羽说,当时整个边区充满恨的声音和恨的光芒。他记录了当时为八路军演出秧歌剧《牛永贵受伤》的情景,“舞台上凄惨痛恨的声音在场上回响,观众一点声响也没有,只在他们眼睛里充满了对敌人愤怒的光”。是否可以说丁玲的短篇小说《新的信念》就是在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与其他在抗日前线涌现出来的作品一样,是饱沾同胞血泪,充满家仇国恨写出的战斗檄文,希望把声声痛苦的呼唤转化为全民族复仇的狂飚雷霆,从而点燃烧向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烈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