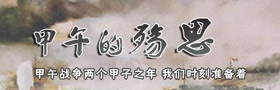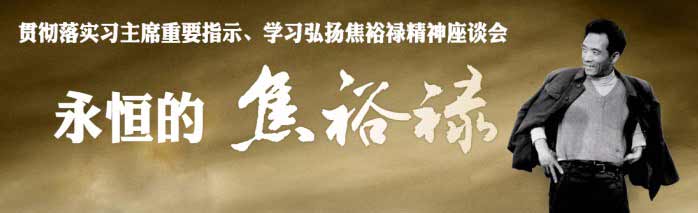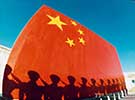记者:对于一些周边问题,有些国人的感觉是,我们似乎谈也不是,打也不是,有的人主张打,有的人主张谈,陷入两难境地,您怎么看?
答:很多人对于中国军队的实力有担心是正常的,因为我军30多年没有参加过战争。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应该把这种担心换成耐心。30年前,邓小平讲,“军队要忍耐”。在军队忍耐的十多年里,国力增长,军力踏步不前。近20年来,中国军队才急起直追,我把这个过程叫做“补课”。对于一个补课学生的期待和一个优等生的期待能一样吗?你要知道,国家先发展了10多年,才让军队“补课”,这个时候我们却要求中国的军力和中国的国力同步,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
尤其是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周边问题敏感,很多人希望中国军队有明显的表现,这显然有点操之过急。现在的国际形势是,美国在鼓动周边国家拱中国的火,因为一旦事端挑起,它就好趁机插手干预,制衡中国的发展势头。美国在等待中国出昏招、走错棋,等中国犯错误。想想看,黄岩岛问题就单纯是中国和菲律宾的问题吗?钓鱼岛问题就单纯是中国和日本的问题吗?会不会出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想明白这些,就知道现在是不是打一仗的最好时机。
可是,确实像你说的,今天的事实的确让人觉得很为难,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打呢,不是时候,不打呢,任人欺负、任人宰割吗?这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动用战略智慧,展现战略定力。战略定力就是,不要以怒兴师、以愠致战,战略智慧就是,你不能不解决问题。完全不解决问题,国际上被人欺负,国内老百姓不答应,那么这个时候,你总要做点什么。怎么做,这就需要掂量,也需要借鉴别人的军事行动的一些启示。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照猫画虎”,但可以由此打开自己的思路。我们总说,军队除了打仗,还可以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什么是非战争军事行动?难道就是抗洪、抗震救灾,就是撤侨、维和、打海盗?非战争军事行动难道就不能开火、不能流血吗?看看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是怎么进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这对我们应有“醍醐灌顶”的启示!
减少战略误判,理性看待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记者:这次哈格尔访华达成了七点共识,有评论说这是哈格尔访华的主要成绩,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从全局的角度来看,哈格尔这次访问中国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他的任务就是要达成一些战略目标,他的成果是和中国在某些问题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这种交流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彼此之间都亮出了底牌,划出了底线,让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诉求是什么。所以,我认为这是中美之间近20年来在军事上最明确的一次协调。(记者:中美之间的交流,虽然态度强硬,但也是一种深入的交谈,开始真正地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会不会带来日本的恐慌呢?)日本一直在中美走近的问题上感到恐慌,中美之间能够达成的任何的谅解、共识或者是协调都使日本有一种被排斥、被出卖的感觉,所以说,日本一直是以一种非常紧张的心态看待中美的每一次接近。(记者:也就是说日本对日美联盟并不是非常自信?)那是肯定的,这是一种“小妾”心态,很多美国的盟友都有这种心态。因为,历史上美国抛弃或者出卖自己盟友的事情并不鲜见,这其实也是夹在大国政治中的那些国家的必然命运。所以,日本在这些问题上不敢对美国一味地信赖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中美之间七点共识中有一点是要发展一种新型的中美两军的关系,这种新型的中美两军关系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双方对这种新型关系的期许有什么不一样呢?现在面临什么困难?
答:新型的两军关系就是互相不视对方为对手,即使出现一些意外或紧急情况,也能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迅速化解危机。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主要看双方有无真诚的意愿。目前,中美两军关系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过去双方除了一些表面上的友好往来以外,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经过哈格尔的这次访问,中美两军之间将来可能会更多地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进行协调、合作,常态化地互通信息,甚至共享情报。如能做到这几点,就会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打下必要的基础。
记者:中美双方在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的互相通报机制、公海海域的海空军事安全行为准则这两个互信机制方面已进入了实质性的磋商阶段,这对两国关系来说是一个推动,但其中有没有隐藏着什么危机呢?
答:我觉得是“机”大于“危”,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军事影响力的外延会不断扩大和延伸,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与美国惯常认为属于它的势力范围发生重合或某种程度的摩擦,如果双方有一种比较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的话,就可以在一旦出现摩擦迹象的时候,迅速通过这一机制进行协调和交流,消除彼此之间的疑虑和不信任,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可能出现的冲突和危机。(记者:您刚说这个机制的出现是“机”大于“危”的,那么“危”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危”,主要是机制虽然有了,但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认真对待这个机制。尤其是美国,出于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往往并不认真对待这类机制。比如说,中国的航母在公海进行演练,美国为了获得情报,在不通报中国的情况下,把它的军舰突然插进来,这就可能导致事情变得复杂,出现麻烦。所以,我认为所谓的“危”,主要就在于制定规则的双方,有多少诚意遵守这个机制。美国往往是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就遵守规则,而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常常率先破坏规则。所以说,有了机制和规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在很多问题上就能很好地协调,关键在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遵守这个机制。
记者:您认为中美两国或者中美两军关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互信的问题吗?
答: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在美国看来对它构成了挑战,只要美国在这方面对中国不信任,双方的协调就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为不管我怎么跟你协调,你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我,协调还有多大的意义?
记者:为什么中国方面一直认为是美国在企图遏制中国,而美国却一直在否认他们想要遏制中国,是双方对“遏制”这个词的理解不一样吗?
答:实际上“遏制”这个定义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中国人喜欢说一句话,“听其言,观其行”。所以我不能只听你的言,还要观你的行。美国人直到今天,直到哈格尔访华,奥巴马访日,言行仍然不一致。如果美国什么时候说,日本人占了中国领土,美国坚决站在中国这一边,我相信双方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弭了,可是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你说你不选边站队,但是你在实际行动上总是支持和中国对立的国家,那怎么可能让我对你的言和行表示一种信任呢?
记者:哈格尔作为第一个经历越战的国防部长,他的个人经历、行为做派会对美国的国防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吗?
答:一个掌权者的个人性格、经历,毫无疑问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决策。哈格尔的个人经历也一定会在美军的战略制定和行为方式上打下他自己的印记,这是肯定的。但实际上,就美国这种体制的国家来讲,个人的印记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的各个机构,包括军队在内,都必须服从国家利益这一最高准则。所以,不管你个人有什么性格经历方面的特点,最终要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有时候美国的决策者也可能对如何实现国家利益、如何保卫国家利益产生战略误判,比如小布什,坚决主张打伊拉克战争。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严重的战略误判。这样的战略误判一旦变成战争行为,就将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给美国的战略利益带来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哈格尔的个人风格并不是最重要的,尽管个人风格强势或弱势有可能导致美国要么获利很大、要么损失很大,就像拉姆斯菲尔德这样一种强势的行事风格,实际上给美国带来了更大的损害一样。但美国政府的高官和美军的高级将领们,其行事准则是以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的,这是不会变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