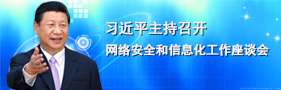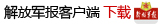守山头的日子倒也苦中有乐。年轻人聚在一起,多的就是力气和精力。我们用罐头盒、炮弹筒之类养花种草美化阵地的做法,得到了上级肯定。到任不久的指导员又张罗着养鱼,对连长说,山上猪养不了,养鱼总可以吧。指导员二十出头,很想有一番作为,鼓励全连骨干“带头看到光明,带头提高勇气,一定要让大家吃上自己养的鱼”。连长是老边防,清楚山上连吃水都困难,靠积攒雨水养鱼显然不太现实,见指导员心血来潮、全连又士气正旺,也不好阻拦,还亲自带上几个兵到修坑道的工兵那里借来水泥,雷厉风行地抹了个养鱼的池子。
阵地养鱼的事后来还惊动了机关的新闻干事,不过看到浅浅的池子中只有十几尾鱼,干事也不好描述,又不好大老远白来一趟啥也没写。那干事毕竟老道,在后来见报的短文中,用了“看到了一片的鱼”这样的描写,让初学写作的我不禁大受启发。想想也是,让人家怎么写呢,写“几条鱼懒洋洋地在水中漂荡”,显然煞风景;写成“成群的鱼儿欢快地游戏”,也有违事实。用“看到了一片的鱼”倒也符合场景。反正我离开阵地之前没见到那池中的鱼身材有过变化,自然也没有吃到连队自己养的鱼。倒是觉得指导员这办法有助于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理解望梅止渴之类的故事。
边境大山中也不是“一无吃处”。当地有种土法制作的酸笋,用肉丝加干辣椒爆炒,十分下饭且极合我口味,但那东西是放到坛子中经过长时间沤过的,做熟之前十几米之外都能闻到那种发酵物的臭味,尤其是在夏天,炊食员每次炒酸笋得捏着鼻子操作。所以,虽然好吃想吃,但谁也懒得动手做。

刚刚从炮校分配来的二排长从小长在江南水乡,文文静静的,第一次帮厨就碰到了炒酸笋。二排长实在受不了那臭哄哄的味道,又不好躲开,竟然夸张地戴上了防毒面具。这一幕恰巧让连长碰上,连长眼睛瞪得像牛。
几年下来,我发现食物单调其实也好处多多。一是锻炼了吃饭速度,至今我吃饭都是三下五除二,每顿绝对用不了十分钟。二是弱化了味觉功能,吃好吃坏一个样,好像吃饭不是为了享受抑或补充营养,纯粹变成了一种任务。及至后来成了家,妻子见我不管吃什么都狼吞虎咽,没等她坐下来就一抹嘴离开餐桌,几次挥着筷子要敲我的头:“你啊你,难道是饿鬼托生的?谁和你抢啊?”
忽有一天梦到了南疆的酸笋,醒来之后竟然有种欲罢不能的感觉,连忙给在那里的战友打电话。战友也是立说立行,第二天就让人到乡间买了往机场送,怎料送到了舷梯又被拦了下来,不用说满舱的旅客,连乘务员也受不了那种味道。待到包了几层塑料袋的酸笋几经周折托运到北京,我正巧外出公务,一家人自然也忍受不了臭味的折磨,又担心左邻右舍抗议,只好“忍痛”扔了。害得我至今也未能重温那往昔的滋味。

消息传到了边防,老战友又把电话打过来:“那东西现在很少有人吃了,街面上卖的也不正宗,要吃出当年的味道,还真得到山里去,要不来一趟吧?”
我知道,分别多年的战友们是想一起聚聚。这个五月,正好是我参加的那场边境保卫战发生三十五周年。看来,真的应该重返一趟那块留下过我五年的青春和许多战友热血的地方了。
——我那可亲可爱的兄弟们,你们可好?
匆匆于2016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