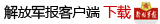1945年冲绳战役中,曾发生过一个真实故事:战前从冲绳移民美国的哥哥被迫参加了美军,留在冲绳的中学生弟弟参加了“铁血勤皇团”,亲兄弟在战火纷飞的故乡遭遇。哥哥带着美军劝降乡亲、寻找家人,弟弟却在身负重伤后仍要死斗到底……最终,妈妈生前的一句话遏止了悲剧:“珍惜生命,只要活着,亲人就能团圆。”
2011年,日本以当事人东江盛勇、东江康治的亲身经历拍摄了电影,片名《最后的羁绊》,题旨为:唯有亲情才能冲破彼此因洗脑而陷入仇杀的绝境。在影片中,分处交战国美国和日本的一家人被割裂得水火不容。哥哥在艰难劝降的过程中,以乡音接近、食物诱惑、承诺生命保障等条件,都难以挽回同仇敌忾、决意赴死的同胞,唯有血缘亲情在最后一刻创造了奇迹。拯救了家人的哥哥却因帮助了敌国,战后留在故乡冲绳种田劳作自我惩罚,心里刻下了深深伤痕。
看这部电影第一遍,很难不被打动,因为亲情伦理这个带有“普世”色彩的超越性主题,在每一个善良者的心里都是沉重的。但细细咂摸日本人表达这个主题的手法,渐渐觉得非常矫情,其藏在皮袍下的“小”,也清晰浮现出来——在对那场战争的回望中,日本人始终有一种难以掩饰的“不甘心”心态。对战争的结果及定性,一时难以做翻案文章,但在具体叙述过程中,仍有很多小动作可做。在细节上巧妙地维护体面和尊严,是该片主创者处心积虑用力之处。
战争责任是上面的,日本人是勇敢的
战后,通过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大致确定了将日本的战争责任归结于政府和军部,而将日本民众“摘”出来的思路;甚至连天皇裕仁也成了被“操纵”和“蒙蔽”的,逃脱了追责。这个基于大国政治运作的做法,让绝大多数日本人长出了一口气,应有的“全民反思”被搁置。在电影创作中,将批评锋芒指向选定的“替罪羊”,就是惯常的手法。
弟弟东江康治是冲绳县立第三中学一年级学生,按日本战时法令,属未满征兵年龄的少年。但在当时上面决定冲绳必须“玉碎”,于是在14岁至17岁的中学生中组建所谓“铁血勤皇团”,与正规部队一起投入战斗。“铁血勤皇团”这一概念,是影片中可以被批评的具象,此外就是课堂上“美英鬼畜”的洗脑宣传。其化身是中学校长和负责军训的日军伍长,这两个面目狰狞的人被确定为片中的“反派”,可供观众拍砖,以承担影片中所需要的“反思”——即“政治正确”之责。
在这个背景下,主创者悄悄塞进了“私货”,极力表现即便是如东江康治等未成年的日本少年,也是不畏强敌而自觉献身的。在日军伍长组织下,他们疯狂地擎着绑缚炸药的竹竿冲向美军战车模型,演练“玉碎”战法。经仇恨教育洗脑后的东江康治,发誓要忘记去了敌国打工的哥哥,带着更小的弟弟剪下指甲留给父亲,宣誓慷慨赴死的决心,甚至请求父亲高呼“万岁”为自己壮行……
影片的重心就这样悄悄漂移了。相信日本观众在观影时,真正的“泪点”是在此处。那场战争虽然输了,但在重温这个少年的“英勇”行为时,日本人仍然可以找到未输的依据。
“附敌”是被迫的,日本心是不变的
据学者云,日本是一个以“耻感文化”为特征的民族。在战争中的通敌和投降行为,是最严重的违背“大义”之举。特别是1941年在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的“战阵训”中,明确规定皇军官兵“生不受囚虏之辱”,彻底断掉了日军官兵在战场上任何怯懦的“私字一闪念”。所以,影片中对于哥哥东江盛勇居然当了美国兵,并且跟着敌人打进了故乡冲绳,主创者如何把话说圆,就是最大的难题。
东江盛勇是战前从日本前往美国农场打工的,并取得了美国籍。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政府将全部日裔关进了集中营,并强征日裔青年服兵役,组建起了著名的442步兵团和MIS(军事情报机构)。东江盛勇参加的是后者,这支日裔秘密部队的职能是对日通讯监听,但后来主要担负在战场上对日军攻心和劝降。
从被迫入伍到加入担负特殊任务的秘密部队,美国政府强令东江盛勇和他的日本同胞一次次签誓效忠美国,彻底否定“日本意识”,不再效忠日本和天皇。在创作这部电影时,已经无法了解当事人东江盛勇彼时的真实内心,但主创者显然不允许他那么轻松就选择了背叛,可以想见日本观众也绝不会接受。于是,表现其在一次次抉择时的艰难就是唯一的手法。
日本战后拍摄的战争电影,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总是安排一个容易冲动的蠢货,把日本人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如不愿意当美国兵、不愿意跟日本作对,甚至对某个怯懦者挥拳相向,而后由主人公表达出迫不得已、“曲线救国”的想法,说服众人。“不当美国兵,不上战场,怎么救同胞?”这时,作为被迫“变节”的东江盛勇的动机,就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谅解。美军军服穿在身,我心依然是日本心——此刻日本观众的道德负疚感,就可能会被感性的泪水稀释。既然“人性”主题已经成为战后的强音,电影主创者当然懂得随大溜。
顺便说一下,日裔美军为美国政府效忠贡献极为突出。如442步兵团是“二战”中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步兵团,也是授勋数量最多的团级单位,共有18143人次获颁各种勋奖章,荣誉包括7次总统集体嘉奖(美军著名的101空降师只获得2次,陆战第1师仅获得3次),21枚荣誉勋章,5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560枚银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铜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这当然不是在“迫不得已”的心态下所能取得的。
面子是重要的,投降是需要台阶的
在战火纷飞的冲绳,作为美国兵的东江盛勇的劝降效果很差,因为很难唤醒一个被深度洗脑的族群,尽管是故乡同胞。影片的主创者再现了这一点,但借此巧妙地塞进了私货:极力淡化日本人被洗脑后的愚昧,凸显他们誓死保卫家园的勇敢和绝不苟且偷生的尊严。
细节上的小把戏比比皆是。比如,主创者当然不敢否定美军何以会兵临冲绳,让日本面临灭顶之灾,但却让你看到:是美军搜索队先开枪打死了“铁血勤皇团”的几位无辜少年后,东江康治才开枪还击打死了美军士兵,招来密集火力而身负重伤。恍惚间,日本人就成了被迫反抗的被加害者。
鉴于日军与冲绳人的负隅顽抗,付出重大伤亡后的美军终于发出命令,实施“三光”战术的大扫荡。主创者当然不放过这个机会,渲染在滚滚烈焰中挣扎的冲绳人的悲惨景象,以控诉美军的残忍。
当“三光”大扫荡迫近东江盛勇的故乡名护市,他获准以一天时间去寻找自己的家人。此时,身负重伤的东江康治被一位农妇搭救,回到父亲和弟弟妹妹身边。这家人正在明治山中的一间草寮中等待最后的命运。
此前,东江盛勇曾救下自己邻居家的一对小姐妹,但这对小姐妹却厌恶身穿美军军服、为敌效忠的东江盛勇,坚决不说出他家的藏身地——主创者对这对小姐妹的“爱憎分明”,无疑也是暗含了肯定和欣赏的。因为美军看管不严,这对小姐妹逃了出去,又回到了藏身的山中,告诉东江家他们的美国兵大哥正在寻找他们的消息。
此时,眼看着次子东江康治命若游丝而无能为力的父亲,毅然决定下山去找自己的长子,希望他来挽救弟弟的生命。父亲跌跌撞撞闯进了美军营地找到了东江盛勇,分离数载的父子在生死攸关的战地重逢。而后,父亲带着长子和美国兵去搭救次子。
一大波荷枪实弹的美军包围了东江康治藏身的草寮,影片的矫情也到了极致。本来父亲下山找大哥是东江康治知情的,当时并未阻止。此刻却亢奋得像一个勇士,于奄奄一息中竟然扣上了钢盔,重新抱起了步枪,对着美军高喊:“美国兵别过来,我是铁血勤皇团员!”此前焦虑不堪,且深知次子已无反抗能力的父亲,这时却踌躇着远远地躲在美军中间不敢靠近了。
于是,作为美国兵的东江盛勇独自上前,面对占据了道德高地的弟弟,只能一迭声地忏悔:“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一分一秒也没有忘记家人,我是你的大哥啊……”本来的拯救者却被迫洒泪以求,给弟弟营造一个“秀场”,帮其冲淡即将投降的心理负担。最后,又搬出母亲生前的话“珍惜生命”,终于让弟弟放下了枪。死去的妈妈的话,再次帮“英勇”的少年兵心理脱敏。于是,影片在兄弟拥抱中终场。
至此,这个故事的主题已经不是哥哥拯救弟弟,而是弟弟给哥哥面子了。日本观众由此当然可以联想,他们的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终战”,并非实在没有办法,而是给了同盟国一个面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