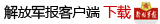从抢粮劫敌到抢耕抢收
最初进驻沁源的日军第69师团伊藤大队,在沁源用尽手段都未组织起“维持会”。1943年1月25日,日军被迫将伊藤大队撤回临汾,以驻长治第36师团222联队鹿野大队接替沁源防务。换防来的鹿野大队,扬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实验”计划。他们除了加强伪化活动,继续玩弄“政治作战”以外,在军事上收缩阵地,主动放弃了一些据点,集中兵力守备沁源城关和交口镇两处。
为了尽快实现组建“维持会”的目的,在2月10日至3月25日期间,鹿野大队不断采取远距离奔袭包围、搜捕群众的办法,并四处张贴布告承诺“凡归来者,给耕牛一头,耕地十亩”,“维持”条件也一再降低。但始终无一人来归,搜捕去的二百余人也先后从据点内逃出。
自此时起,沁源军民对日军从围困逐步转为主动出击。
春节过后,群众把互助粮和救济粮吃光了,新的困难又来了。当时,城关有个老乡趁黑夜回村,把自家磨盘下埋藏的3斗小麦取了出来。围困斗争指挥部受到启发,马上抽两名公安队员和四名民兵骨干组成“抢粮”小组,利用日军夜间警戒疏忽,摸进城关日军据点抢粮。不但抢粮得手,还摸清了日军的驻地和哨位。据报,此时的沁源城,除了敌伪兵营外,只住有三户“人家”:一家“随军合作社”,一家“随军妓院”,一家“蒸馍铺”,还有就是已经饿得到处乱窜、与敌人争食的四百多条野狗。日军绝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抢粮小组能从他们嘴里把粮食抢运出来。这次行动成功后,指挥部立即组织了大规模的抢粮队伍,并很快发展到二沁大道和安沁大道两边的各个村镇,大约有5500余人参加了抢粮斗争,在20天左右的时间里,共抢出7400余石粮食。沁源城内北街有位妇女郭效兰,连续几次摸回家,背出了八石粮食。另一个崔家寡妇,一次竟摸到城北街镇武楼日军哨兵附近,把敌人装好的五斗小麦也扛了出来。
参加者胆子越来越大,“抢粮运动”又逐渐发展成为“劫敌运动”。人们先是回家背自己埋藏的粮食,后来就摸进敌人的据点,拿敌人的东西。有一个双腿残废的退伍军人,一天夜里爬进了敌人的马棚,趁马夫鼾声大作,拉了一匹马悄悄爬了出来。等敌人发觉时,他已骑上马扬长而去。一个民兵摸进据点,把敌人一箱子弹也扛出来了。交口据点的敌人共有六副水桶,一个夜晚便被劫一空。甚至连井上的辘轳、碾盘上的转轴,也被群众拿了出来,弄得敌人几乎连水也喝不上。有的据点的伪军,找不到碾子磨盘,只好吃麦粒子。伪山西《新民日报》特派员董长庚随日军到沁源,在其所采写的通讯里记述日军当时的处境:“沁源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
4月19日夜,在围困斗争指挥部李懋之、刘开基直接指挥下,由38团第2营带领县游击大队(大队长朱秀芝)及一区的游击队和民兵共1200余人强袭沁源城关据点,抢救出被日军抓捕的180余名群众。这次战斗共杀伤日伪军250余人,缴获步枪160余支,轻机枪2挺,烧毁仓库粮台4座,草料场3处。此次大规模强袭县城,对敌我双方心理影响极大,就连被日军裹胁在城内的几个老年士绅也乘乱逃出城来。
冬去春来,进入播种季节,群众焦心无法下种,一时人心惶惶。这时太岳区党委提出了“劳武结合,游击生产”的号召,指挥部组织起了抢耕队、抢种队。白天在距离敌据点较远的地里耕种,夜晚潜入敌据点附近地里耕种。有时被碉堡上的敌人发现了,部队和民兵在前面乒乓打枪掩护,老百姓在后面仍扶犁摇鞭,不慌不忙地耕种。昼夜轮番抢耕,终于在枪炮声中把所能耕种的土地全部耕种上了。
进入夏季小麦成熟时节,敌人从外地拉来大批民夫抢收,指挥部又组织部队和民兵,以抢收对付抢收。白天敌人抢收时,我方四处打冷枪,闹得敌人六神不宁。待敌把麦子割好捆好,我方突然发起攻击。敌人拉来的民夫听到枪声一哄而散,趁着天黑,我方抢收队即全部出动,将敌人收割的麦子搬完。
在1943年夏季武装抢收运动中,共抢收小麦15000余石;加上对日军据点的抢粮斗争,夺回了大批粮食,解决了军民吃粮问题。此外,又组织商人到晋南洪洞、霍县(今霍州市)等地贩运棉花、布匹及其他物资,解决了群众的衣食问题;组织民间医生开办简易诊所和药铺,给群众看病吃药,克服了重重困难,为长期围困日军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精神信念。
1943年7月16日,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在日记中记下了沁源围困斗争的意义:“……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锻炼了党,锻炼了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各阶层;提高了民族觉悟,发挥了民族气节”。陈赓特别提到,围困沁源是敌我双方顽强斗争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只要我们善于领导,群众是不会离开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