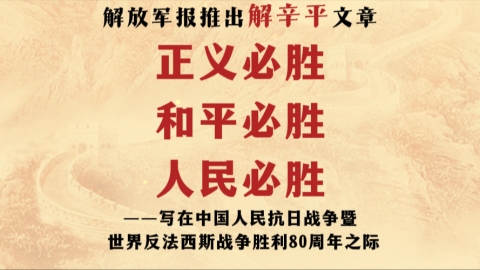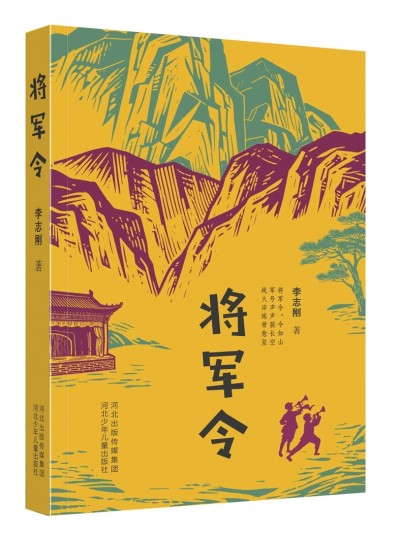
▲《将军令》,李志刚著,河北少儿出版社2025年7月
为什么我们要记住这些少年?
——《将军令》创作手记
■李志刚
写下《将军令》书稿的最后一句话时,窗外的太行山已经变得蓊蓊郁郁了。从隆冬到盛夏,我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心灵跋涉。结稿那天,我再次来到涉县赤岸村。不甚高大的山岭,油光水滑的石巷,棋盘一样错落在山上山下的小小院落,还有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小院里蓬蓬如云的紫荆和丁香,都让我感到无比亲切。漫步将军岭,岑寂的山林中只有淙淙泉响,声声蝉鸣。恍然之间,泉水如军号一样嘹亮,蝉声如唢呐一样高亢。我仿佛又听到喜旺吹响了《将军令》。这曲调雄壮、苍茫、悲壮,有着金戈铁马之声。这石破天惊的音调,犹如太行山般突然拔地而起,带着肃穆雄壮的威严屹立于苍茫大地。
历史的回响:与烽火少年的隔空对视
从唐代宫廷传到近代民间,《将军令》早没了黄钟大吕的华贵,却多了几分凡人烟火的鲜活。传到太行山时,这调子已沾染了土气,长出了松针的锋芒。多年之前,我在太行山深处第一次听到唢呐演奏的《将军令》。唢呐的声调脆生嘹亮,犹如山鹰长唳。悠悠荡荡之间,群山和鸣不绝。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从吹唢呐的老农口中得知,这曲子来自“八路军太行山剧团”中一名小八路宣传员。当年,剧团的这些孩子们骑着骡马,冒着敌人的枪炮,一路颠簸着走过漫漫苍山,浩浩烽烟,在八百里太行山里留下了唢呐久远的回响。当再次来到太行山深处的黄崖洞采风时,我站在小号手崔振芳的雕像前,长久地静默。一位十七岁的少年,面临汹汹日寇的偷袭,毅然吹响了军号报警。最终,他抱着心爱的军号倒在了太行山雄阔的怀抱。面对烽火狼烟,这些少年承受着比成人更大的精神和身体煎熬——饥饿、伤痛、迷茫、愤怒、憎恨,甚至直面死亡的恐惧。抗战时期的孩子们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坚强,不但承受了他们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重压,甚至还挺直腰杆扛起了本该由成人肩负的责任。
军号与唢呐,汇成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抗战交响曲,也映射着太行山烽火少年的峥嵘岁月。它们像烈酒一样烧灼着我的心。我开始频繁往返于太行山区,在石板路的青苔里探寻少年的脚印,在老人们的讲述中追忆少年的故事。我想让红生的军号与喜旺的唢呐在文字中相逢,让那些被烽火吞没的少年身影,重新站在太行山的崖畔。让更多的人铭记,曾经有一群少年用军号和唢呐,在太行山深处吹亮了黎明。

儿童视角:战争的诗意叙述
儿童视角的选取,不仅仅出于我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更多的是对那个时代孩子们苦难和生存状态的关切。当我在太行山走访时,发现一个惊人现象:老人们关于抗战最鲜活的记忆,大多停留在他们七八岁的年纪。有一位老人清晰记得“子弹打在石头上溅起的火星像明火虫(萤火虫)”,却记不清那场战斗的具体日期。这种记忆的筛选启示了我:或许只有通过孩子的眼睛,才能展现战争最本真的肌理。在《将军令》中,我刻意构建这种“天真滤镜”:红生眼中的枪声是“过年的鞭炮”,日军飞机是“长翅膀的怪鸟”。即使面对最残酷的死亡,在红生看来,谷米哥“一定会踩着一朵云,或者踏着一朵浪上岸”。这种诗意化处理不是对残酷的消解,恰恰相反,当红生接过谷米哥的军号时,孩童认知与战争真相的碰撞,反而迸发出更为强烈的悲剧力量。激励少年们在抗战岁月中成长的是什么? 书中两个意象的反复出现形成有趣对位:红生总在寻找“最亮的北极星”,那是长征路上老吴叔教他的生存法则;喜旺执着于“崖畔的老松爷”,象征着乡土赋予的精神韧性。当两个孩子在山巅将唢呐与军号共同举向天空时,两种角度的认知世界终于合流——革命理想主义与民间生命哲学,在少年们仰望的夜空中达成了和解。
芸芸众生:太行山的“精神群雕”
在《将军令》描述的太行烽火中,我专注的不仅仅是烽火少年,还有太行山里的朴实百姓。靠山爷、王秀才、春生叔、福田叔、福田婶……他们就如清漳河的浪花与太行山的岩峰,既各有棱角又相互映照,共同织就了抗战年代里太行民众的精神图谱。他们身上浸润着太行的土气与骨气,在战火中展现出传统与革命交织的生命力。春生叔是我着墨最多的一位成年人,赛戏里的忠义与战场上的勇猛在他身上完成了共生。这个角色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让《将军令》既保留松针的清香,又融入硝烟的灼热,成为传统精神向革命信仰过渡的活态样本。而老吴叔,就像是一块被清漳河浸润多年的太行石。不耀眼,却带着山水淬炼的厚重。他的军帽永远粘着灶灰,裤脚总布满草屑,肩头那口大黑锅的锅沿被磨得发亮,却在烽火岁月里熬出了最动人的革命温情。这个角色的魅力,在于他把“战士”与“父辈”的双重身份,融进了太行山的沉默与清漳河的缠绵。还有福田婶,她是“后方脊梁”的代表。她纳鞋底时“一寸大的鞋底要纳九九八十一针”。她在柿子树下守望时,把对丈夫的牵挂织进鞋垫的连翘花纹里。她没有豪言壮语,却用“丈夫赴战场、妻子守家乡”的日常,写就了最动人的家国温情。相较于这些“小人物”,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首长们却着墨甚少。但他们在红生、喜旺这些少年的眼中,就是太行山的影子。他们用高大的山脊,将这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印入了热气腾腾的土地。这些人物在烽火中相互支撑,让太行山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更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就像清漳河绕山而行,传统与革命、坚守与奉献在他们身上完成了最动人的融合。
今天,当我们回望红生与喜旺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缅怀历史,更是为了思考:在新时代,中华少年的成长是否仍然需要某种“号声”的召唤? 是否仍然需要像太行山那样坚实的土壤?《将军令》里的少年们,用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无论是军号的嘹亮,还是唢呐的苍凉,最终都将汇入历史洪流,成为永不消逝的时代回响。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市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