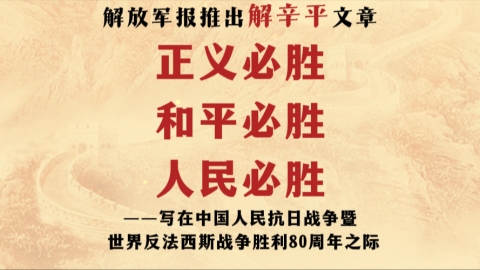在精神与情感世界深度开掘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化
■杜学文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新中国文艺的重要一翼,大量革命历史题材优秀作品,不仅为我们形象地勾勒出了中国革命历史的生动画卷,亦形成了相应的审美范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一般而言,它们比较关注重大历史事件,洋溢着蓬勃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注重描写人物性格,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不仅回溯了革命历史,亦在这种回溯中弘扬了民族精神,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许多探索,显现出新的面貌。以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两部长篇小说为例,他们在艺术表现层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提升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力。
徐怀中的长篇小说《牵风记》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以青年学生汪可逾在抗战期间奔赴延安途中滞留在太行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至挺进大别山期间的人生经历为主要情节,充满诗意地描写了她的命运际遇,表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然。其中的宋代古琴如同传统戏曲的道具一般贯穿整部作品,具有极为明显的隐喻意义。小说基本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但时时折射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这种虚与实的统一又恰似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留白,于无中写有,在有处见无,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当代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一部难得之作。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被视为“先锋”作家的孙甘露在这部小说中强化了“叙事”的复杂性、神秘性,设计了一个在“未知”中求“有知”的情节结构与人物关系。那些战斗在隐蔽战线的英雄身上闪射着革命者坚韧、执守、奉献与智慧的品格,洋溢着沉入人内心深处的理想情怀与奋斗精神。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代艺术在思想、审美、创造诸多方面的巨大潜力与可能性。其表现手法的新变化与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刻画使这些作品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艺术品质。
这种新变化,也体现在某些区域性的创作现象之中。作为中国文学重镇的山西文学,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也表现出新的气象。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长篇小说选刊》特别出版了“山西作家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专辑”,收录了张卫平的《红色银行》、郭天印的《铁血围城》与蒋殊的《红星杨》三部长篇小说。
张卫平的《红色银行》,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于吕梁山区兴县创办西北农民银行的革命历史。尽管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很多,但表现抗战期间党领导的金融工作的作品却甚少。之后,张卫平又创作了另一部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英雄年代》。作者的描写更多地侧重于普通民众,力图揭示那个特殊年代里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演变与升华,以及在民族危亡时刻个人的成长与奉献。他们是历史洪流中的芸芸众生,更是具有民族气节的时代英雄。
郭天印的《铁血围城》,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山一带发生的著名的“沁源围困战”。其突出之处在于把真实的历史事件以小说的方式进行重构,强调了叙述的传奇色彩,挖掘了人物的精神内涵。蒋殊近年来创作了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如《重回1937》《再回1949》等。她的作品主要集中于表现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普通战士平凡人生中的高贵品格。
《红星杨》的创作灵感来自八路军总部王家峪由朱德总司令亲手种植的树芯中有红色五角星的杨树。人们认为这种杨树有着神奇的含义。由此,作家虚构了杨家将后人杨留贝等一群孩子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中由懵懂无知到逐渐成长,成为革命战士的故事。其特别之处在于以红星杨的意象展现出战争年代各式人物的精神世界,以及由“红星杨”喻示的不畏艰难的精神,表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坚韧的生命力,使小说具有了一种诗化的意味。
近年来,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另一种特质是更注重个人情感与生命价值的表达。以往的同类作品在题材选取方面基本有两个维度。一是对真实发生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写。这种描写力求体现出“史”的真实性,强调“群体性”与“客观性”。另一类则是虚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这类作品尽管有较大的表现空间,但仍然比较重视“群体性”与“客观性”的呈现。
在这个维度上,近年来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不论真实还是虚构的历史事件,都比较注重表现个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物的精神情感世界。以余艳的报告文学《板仓绝唱》《杨开慧》为例,作品虽然也描写了当时艰难残酷的革命斗争,表现出某种意义上的“群体性”,但更为强调的是作为个人——恋人、爱人、母亲与战士的杨开慧,更注重对人物精神与情感世界的描写。因而,作者为我们塑造的是一个极具情感色彩的、具有坚定信念与精神力量的人物形象。
长篇小说《觉醒年代》虽然是作者龙平平在同名电视剧的基础上创作的,但由于电视剧本身即注重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在小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表达,使其人物的精神情感内涵更为强烈,作为“革命者”的个人色彩更为典型。特别是陈延年、陈乔年的形象尤为感人。这种新变化也强化了小说所要表现的“觉醒”寓意——不是某个先行者的觉醒,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在一个时代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变化,也反映出近年来中国文学的积极变化。这种变化使我们看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在新时代的新收获、新拓展,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