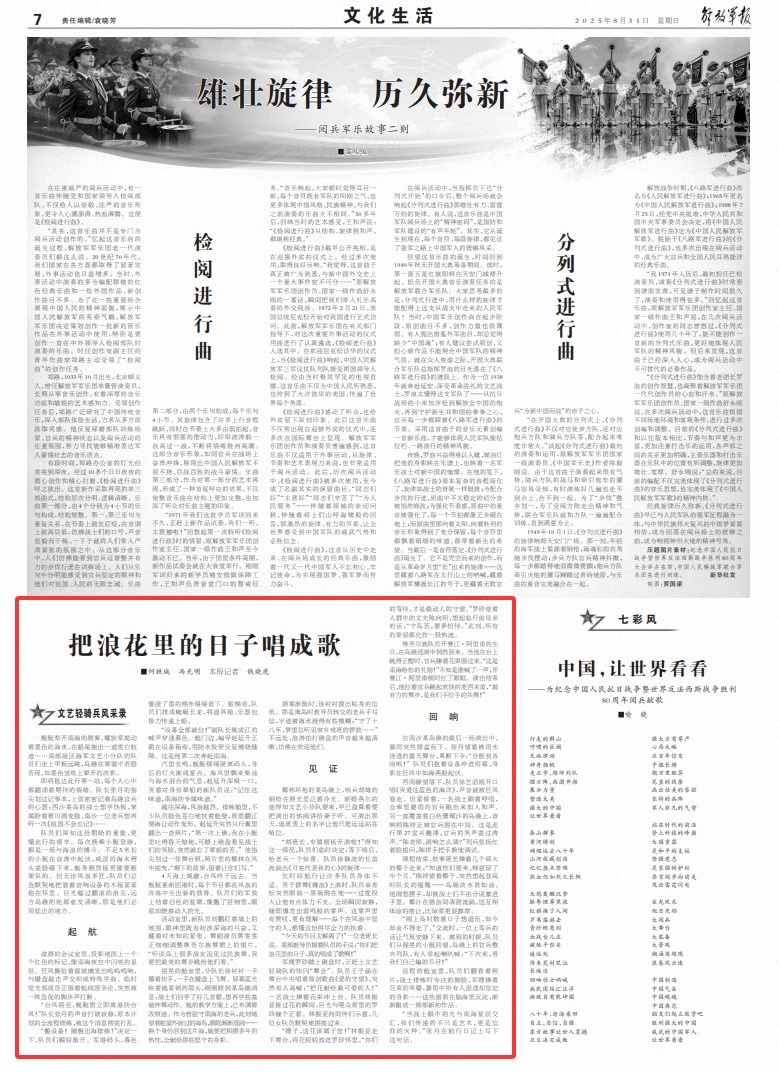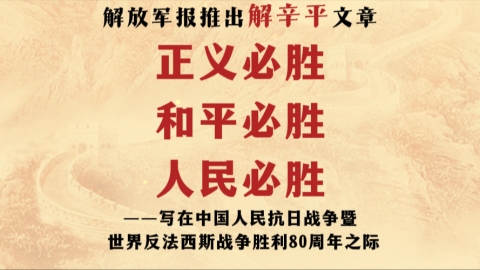把浪花里的日子唱成歌
■何铁城 冯光明 解放军报记者 钱晓虎
舰艇犁开南海的晨雾,螺旋桨搅动着墨色的海水,在船尾拖出一道雪白航迹……南部战区海军文艺小分队的队员们走上甲板远眺,岛礁在雾霭中若隐若现,如墨色宣纸上晕开的淡影。
即将抵达此行第一站,每个人心中都翻涌着期待的情绪。队长张丹的指尖划过记事本,上面密密记着岛礁官兵的心愿:西沙某岛的战士想学快板,家属盼着看川剧变脸,南沙一位老兵想再听一次《祖国不会忘记》……
队员们深知这份期盼的重量,更懂此行的艰辛。每次换乘小艇登礁,都是一场与海浪的搏斗。不足5米长的小艇在浪涛中起伏,咸涩的海水劈头盖脸砸下来,艇身剧烈摇晃像要散架似的。但无论风浪多狂,队员们总会默契地把装着音响设备的木箱紧紧抱在怀里。目光越过翻滚的浪尖,远方岛礁的轮廓愈发清晰,那是他们必须抵达的地方。
起 航
凌晨的会议室里,投影地图上一个个红色的标记,像南海夜空中闪亮的星辰。狂风撕扯着窗玻璃发出呜呜鸣响,与键盘敲击声交织成特殊序曲。临时党支部成员正围着航线图争论,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
“台风将至,舰艇需立即离港防台风!”队长张丹的声音打破寂静,原本计划的全流程排练,被这个消息彻底打乱。
“搬设备!随舰出海排练!”决定一下,队员们瞬间散开。军港码头,暮色像浸了墨的棉布缓缓垂下。舷梯旁,队员们排成蜿蜒长龙,将道具箱、乐器包接力传递上船。
“设备全部就位!”副队长姚成江的喊声穿透暮色。舱门边,编导赵延升正跪在设备箱旁,用防水胶带反复缠绕缝隙。这是他第二次奔赴南海。
汽笛长鸣,舰艇缓缓驶离码头,身后的灯火渐成星点。海风里飘来柴油与海水混合的气息,赵延升深吸一口,笑着对身旁晕船的新队员说:“记住这味道,南海的专属味道。”
越往深海,风浪越烈。排练舱里,不少队员脸色苍白地扶着舱壁,胃里翻江倒海让动作变形。赵延升突然从行囊里翻出一沓照片:“第一次上礁,我在小艇里吐得昏天暗地,可踏上礁盘看见战士们的笑脸,突然就忘了晕船的苦。” 他指尖划过一张舞台照,照片里的椰林在风中摇曳,“剩下的故事,留着让你们写。”
4天海上规避,台风终于远去。当舰艇重新回港时,每个节目都在风浪的淬炼中生出新的筋骨。队员们的军装上结着白色的盐霜,像撒了层细雪,眼底却燃着动人的光。
活动室里,新队员刘鹏盯着墙上的地图,眼神里既有初涉深海的兴奋,又藏着对未知的紧张。舞蹈演员蒋雯雯正细细调整维吾尔族舞裙上的银片,“听说岛上很多战友没见过民族舞,我要把最美的舞步跳给他们看。”
摇晃的舱室里,分队长徐衬衬一手攥着扶手,一手在键盘上飞舞。屏幕蓝光映着她紧锁的眉头,刚刚收到某岛礁消息:战士们自学了好几首歌,想再学些基础伴舞动作。她的教学方案上,已布满修改痕迹。作为曾驻守南海的老兵,此刻她望着舷窗外掠过的海鸟,眼眶渐渐湿润——换个身份回到这片海,她要把积攒多年的热忱,全献给那些坚守的身影。
晨雾渐散时,徐衬衬摸出贴身的信纸。那是离岛时教导员转交的老兵手写信,字迹被海水浸得有些模糊:“守了十八年,梦里总听见家乡戏班的锣鼓……”不远处,浪涛拍打礁盘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仿佛在欢迎他们。
见 证
椰林环抱的某岛礁上,哨兵胡雄的钢枪在晨光里泛着冷光。新婚燕尔的他得知文艺小分队要来,早已盘算着要把演出的热闹讲给妻子听。可演出那天,值班表上的名字让他只能远远站在哨位。
“胡班长,专属剧场开演啦!”得知这一情况,队员们临时决定:等下哨后,给老兵一个惊喜。队员徐静波的长笛流淌出《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旋律……
长时间航行让许多队员身体不适。男子群舞《搏浪》上演时,队员章青松突然眼前一黑栽倒在地——过度投入让他有点体力不支。全场瞬间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里有赞叹,更有理解——每个在风浪中坚守的人,都懂这份拼尽全力的执着。
“今天的节目太解渴了!”一位老班长说。某部教导员握着队员的手说:“你们把浪花里的日子,真的唱成了歌啊!”
军嫂罗珍踏上礁盘时,正赶上文艺轻骑队的快闪“舞会”。队员王子涵在舞台中央唱着原创歌曲《爱的守望》,突然有人高喊:“把花献给最可爱的人!” 一名战士捧着花束冲上台。队员林振亚接过花的瞬间,目光与观众席里的罗珍撞个正着。林振亚向同伴们示意,几位女队员默契地围拢过来。
“嫂子,这花该属于您!”林振亚走下舞台,将花轻轻放进罗珍怀里,“你们的等待,才是最动人的守望。”罗珍望着人群中的丈夫陈向阳,想起临行前母亲的话:“守岛苦,要多担待。”此刻,所有的委屈都化作一股热流。
维吾尔族队员开赛江・阿里甫的生日,在岛礁巡演中悄然到来。当他在台上跳得正酣时,官兵捧着花束围过来。“这是南海给你的礼物!”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开赛江・阿里甫顿时红了眼眶。演出结束后,他拉着官兵跳起欢快的麦西来甫,“最有力的舞步,是我们手拉手的共舞!”
回 响
在南沙某岛礁的最后一场演出中,暴雨突然倾盆而下。张丹望着被雨水浇透的露天舞台,果断下令:“分散到各岗哨!” 队员们抱着设备冲进雨幕,身影在狂风中如海燕般起伏。
西南瞭望塔下,队员徐艺滔刚开口唱《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声音就被狂风卷走。但紧接着,一名战士跟着哼唱,仓库里避雨的官兵跑出来加入和声。另一座覆盖着白色珊瑚沙的岛礁上,音响师陈祥正被官兵围在中间。这是此行第27堂兴趣课,官兵的笑声盖过涛声。“陈老师,混响怎么调?”列兵张扬红着脸提问,陈祥手把手教他调试。
课程结束,炊事班长捧着几个硕大的椰子走来:“知道你们要来,特意留了半个月。”陈祥望着椰子,突然想起登岛时队长的提醒——岛礁淡水贵如油。他刚想摆手,却被战士们不由分说塞进手里。椰汁在唇齿间清甜流淌,这互相体谅的推让,比琼浆更显醇厚。
“刚上岛时数着日子想退伍,如今却舍不得走了。”交流时,一位上等兵的话让气氛安静下来。离别的时候,队员们从摇晃的小艇回望,岛礁上的官兵整齐列队,有人举起喇叭喊:“下次来,看我们自己编的节目!”
返程的舱室里,队员们翻看着照片:战士排练时专注的侧脸,军嫂捧着花束的笑靥,暴雨中所有人湿透却坚定的身影……这些画面在脑海里沉淀,渐渐酿成一部部新的作品。
“当战士眼中的光与南海星辰交汇,我们传递的不只是艺术,更是信仰的火种。”张丹在航行日记上写下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