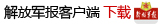1934年1月中旬,蒋介石还在忙于镇压“福建事变”,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由博古主持,通过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同时补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
六届五中全会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被载入中共党史史册的。它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对世界和中国形势分析的错误观点,盲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并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会议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同时继续批判“富农路线”,贯彻错误的下层统一战线策略,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以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继续在党内和红军内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鉴于此时十九路军败局已定,会议认为蒋介石即将对苏区发动更为猛烈的进攻,为此做出了关于紧急动员全部力量夺取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决定。为贯彻这一精神,同时也为了总结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确定政治工作的方向、任务和办法等,红军总政治部决定召开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2月7日下午,“对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对创造和扩大百万铁的红军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政治会议开幕了”。出席会议的有中央红军各军团、中革军委直属队、湘赣军区、湘鄂赣军区、闽浙赣军区、江西军区、福建军区、闽赣军区、粤赣军区和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兵站医院、地方武装代表共258人。红四方面军、红三军、红二十五军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大会主席团由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5人组成。会议期间,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作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王稼祥作《关于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介绍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朱德就红军政治工作问题发表重要演说,周恩来作《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演说,李德发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问题的讲话。共有30多人在大会上发言。其中,陈云就争取白军工作、凯丰就青年团与青年工作、张爱萍就赤少队与红军的关系、罗荣桓就训练赤卫队成为红军预备队等问题分别作了发言。会议结束时,王稼祥作会议总结,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致闭幕词。
这次会议是红军创建后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在战斗环境中来讨论战斗的政治工作”,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方针、原则和方法等问题作了一些正确的阐释,如在大会发言中多次强调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确立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为着实现整个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规定了“从政治工作来领导提高红军中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要求,提出了“加强与改善政治教育工作”“造成铁的红军”的任务,系统总结了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强调了加强游击队、赤少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政治工作必须改进工作方式等。这对红军乃至后来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这次会议毕竟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苏区登峰造极、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被解除的情况下召开的,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如认为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是同敌人“最后的决战”,是“解决谁胜谁负”的问题,并多次把带有游击性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作为所谓“游击主义残余”“浓厚的保守主义”进行批判,要求“扩大百万铁的红军”,以“持久战”“阵地战”“堡垒战”来“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等错误主张。李德在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更是极力鼓吹“左”倾错误思想,提出了反对堡垒主义的新战术——“短促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就是敌人筑碉堡红军也筑碉堡,然后对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推进筑垒的敌人,乘其立足未稳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种战术要求极高,既要有准确的情报和判断,又要集中精干的兵力,还要和敌人作阵地战,更要能积极地结束战斗。由于敌人重兵集结,弹药充足,火力较强,四面呼应,红军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而这种战术,限制了红军的主动性。红军不能去主动调动敌人,只能坐等敌人出碉堡时以求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