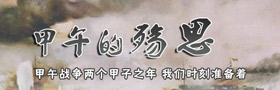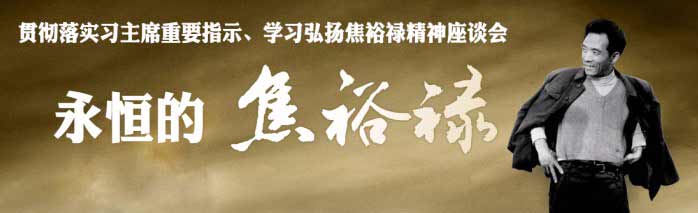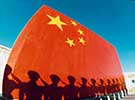我忽然心生感动。从第一次在景洪见到澜沧江投入它的怀抱,到今天涉足澜沧江上游,已经过去了整整36年。当年不谙世事的一名北京知青,如今成长为共和国将军,而澜沧江所见证的,正是我永远怀恋的“兵之初”。
一杯“藏乡醇”摆在面前,随行记者要与我“为36年干杯”。我叹:“又见澜沧江,两眼泪汪汪”,随即一饮而尽。
我是在那个动乱年代被上山下乡的大潮卷到西双版纳的。1969年5月中旬,我们一批北京知青赴云南“屯垦戍边”,先是乘坐4天4夜的火车到昆明,然后换乘解放牌卡车,一路晓行夜宿又走了4天,终于来到西双版纳自治州州府所在地景洪县。
由于最后那天行程较短,车过景洪大桥时,天色尚早。我们靠着车厢,贪婪地欣赏着从未见识过的热带雨林,当澜沧江奔来眼底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大呼小叫起来。当时,我们的激动与这条大江的从容形成鲜明对比:在西双版纳午后的阳光下,澜沧江像一条慵懒的巨龙,扭动着庞大身躯不紧不慢地游向远方。
车队驶进宿营地后,我们最渴望的就是洗澡。那时昆明到景洪的公路还是土路,一路行车,尘土飞扬,知青们坐在车厢的行李上,个个都成了土猴儿。到哪儿洗澡?澜沧江呀!放下行李,我们一路打听着来到江边,换上游泳裤就跳了进去。天热水暖,在浅水处嬉戏不过瘾,不知谁说了一句:“敢不敢游过去?”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凭着在北京游泳池里练出的那点水性,居然夸口:“这才几百米呀,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我和另外两个知青根本没有细想,便结伴游向对岸。
开始倒没觉得怎样,尽管越往前游水流越急、水温越凉,可不知深浅的豪情完全抑制了面对激流的紧张,我们一边畅游一边说笑。等游到对岸回头一看,发现我们已被水流往下游冲了很远,这才感到后怕。尤其是想起途经昆明时,曾听一位到过西双版纳的中年妇女说起,澜沧江里有一种叫做“席子”的生物,远看像一领草席随波逐流,一旦遇到人畜等活物便会顺势卷起,将猎物包裹其中慢慢消化掉。这个传说令人心生恐惧,怎么办?没办法,只能游回去。忐忑中,我们踩着遍地卵石往上游走了很远才下水。这次谁也不敢说话了,甚至不敢把头扎入水中,眼睛紧张地搜索着水面,随时准备同不期而遇的“席子”进行搏斗。
时至今日,我也没有搞清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席子”,但却实实在在领教了澜沧江的神秘与冷峻。
事实上,这只是我与澜沧江结缘的开端。
那时候,知青的口号是“扎根边疆干革命,广阔天地练红心”。可年轻人毕竟好奇心盛,又被“文革”纵容得纪律涣散,分配到大勐龙东风农场东方红分厂仅一个星期,我们几个北京知青便找了个借口离开生产队,翻山越岭上景洪,又一次来到澜沧江边。这一回,我们没有游泳,而是乘船去了橄榄坝。理由很简单:都说不到西双版纳等于没到云南,而不到橄榄坝等于没到西双版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