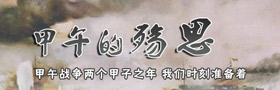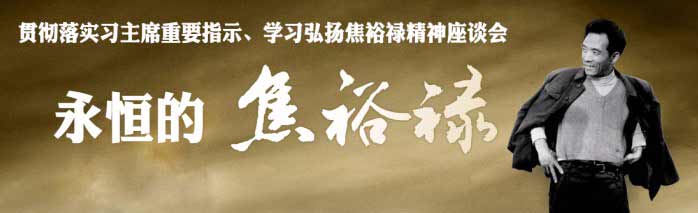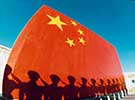记忆中,那时的橄榄坝有一条从江边通往傣族村寨的土路,浮土很厚,连高大的椰树都被染得灰头土脸。尽管如此,这些南国椰风还是让我们领略到异域的热带风光。更难忘的是,我们在江边一家食馆里,吃到一种名叫“江团”的鲜鱼,据说是澜沧江特有的,鲜嫩无比,至今回想起来,仍口有余香。
橄榄坝之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生产队显然宽容了初来乍到的小知青的自由散漫。这反而让我感到内疚,后来我们玩命干活儿,以“自觉接受再教育”的姿态赢得了老职工们的认可。只是,我在农场干了不到一年,就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被当地驻军特招入伍了。1970年3月,我在云南省思茅军分区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光荣的边防军人。
当兵之后搞报道,我的军旅生涯乃至新闻学步均由此开始。那些年,我到过景洪、勐海、勐腊等地多个边防连队,足迹所至大多与澜沧江有关。
记得在澜沧江流经边境的地方,有个小镇叫关累,如今已成为沿湄公河入境船舶最先停泊的码头,也是云南省与缅甸、老挝、泰国直接进行经贸交往的重要水路通道。1972年夏天,我和两位同事去关累采访某边防团四连,他们守卫的澜沧江段属于界江,对岸是缅甸,下游是湄公河。当时,橄榄坝以下的江段还没有通航,关累处于大山夹峙中,交通不便,湿热异常,而境外又不太平,四连任务很重,生活很苦。有一天,我们参加连队巡逻,与官兵一起穿越莽莽森林,从山巅一直下到江边,历尽艰辛。望着眼前翻滚的江水和对面暗伏杀机的大山,我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人使命有了更加深刻的体验。
1973年全国陆地边防工作会议之后,西双版纳军分区正式组建,并从思茅军分区抽走一批骨干,而我则留在思茅,去景洪方向的机会少了。可作为连接两个地区的纽带,澜沧江依然流淌,我和版纳战友的联系依然紧密。
参加野营拉练是那段时间我经历的一件大事。1973年底,思茅军分区组织部队进行野营拉练,在参谋长亲自草拟的上报原昆明军区的请示电中,一句“澜沧江斜切我部防区”的表述,道出了此次跨越澜沧江拉练的决心。
当年的日记显示:我们11月26日从思茅出发,一路避开大道走深山,经过连续4天的徒步行军,于29日下午抵达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境内的澜沧江边。野营拉练,强调的是“野营”不扰民,况且,周围荒无人烟,我们只能就地取材,在江边沙滩上搭建起由一片窝棚组成的宿营地。
12月1日,部队开始渡江,漂浮器材主要是头一天捆扎的竹筏。看起来,那段江面并不宽阔,江水流速每秒2.5米,横渡似乎不成问题。谁知,庞大的竹筏一旦被拖下水,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却难以控制,好不容易划到江心,江水陡然湍急,流速达到每秒5米,瞬间便将竹筏冲远,战士们只得弃筏跳江,只身游回。再用小竹筏试渡,虽然划过去了,可登陆点竟被冲至下游1公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