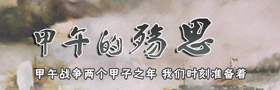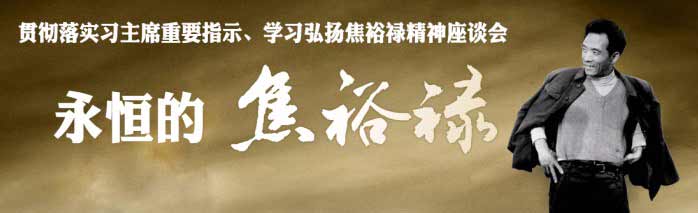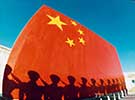“导师就像老父亲!”严高鸿的学生、武警北京指挥学院教员张琳琳说:“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他背着我们走、拉着我们走、扶着我们走……在他的心里,每一个学生都是自己的孩子,他瘦削的肩膀上,扛着大山一样的爱。”
张琳琳记得,2009年4月,导师的儿子严文昊快结婚了,这时张琳琳的博士论文修改定稿也到了节骨眼上。为了审改张琳琳的论文,严高鸿几乎无暇顾及筹备儿子的婚礼。儿子婚礼当天的早晨,严高鸿还在推敲着……
至今,张琳琳仍然完好地保存着导师历次审改的毕业论文手稿,叠在一起足足有一尺多厚。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严高鸿从头到尾审改了四五遍,几乎每一页都写满了红字,连注释他都逐字逐句核对过目。
“抚摸着导师密密麻麻的笔迹,能感受到一种暖暖的温度!”说到这里,张琳琳泪水夺眶而出:“一篇博士论文就是一本书啊!我敢说,让导师自己写一本书,都未必会花这么长的时间、费这么多的心血。导师要尊重学生的观点陈述,还要尽量照顾学生的表达风格,因人而异,字斟句酌,他怎么能不累呢?”
“要不是导师资助,我是没法读博士的。”学生袁周说起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当年,我工资很低,给妻子治病花了不少钱,家庭负担非常重,心想算了吧,这个博士不念了!”
“导师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说,你能考上这个博士,机会难得,希望你珍惜。第二天,他拿了一万块钱给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可以说,没有导师就没有我的今天。”
“其实,导师也不富裕,师母是工人待遇,早已下岗,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块钱。平日,导师把省下的钱差不多都给师母买了养老保险……”
■“导师在世时,我们觉得他可亲;导师走了,我们才感到震撼”
博士生刘大勇,是最后一名聆听严高鸿讲评的学生。
回忆去年12月18日上午的情景,刘大勇至今历历在目——
“那天,严老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15分钟的讲评。报告会中途休息的时候,他走出会场。开场时,他又准时走回了座位。我当时以为他出去抽了根烟,后来才知道,他感到很难受,去隔壁房间的沙发上躺了一会儿。10分钟以后,大家发现他总是不说话,转头看他时,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事后,我看到一张在开题报告会现场用手机拍摄的照片。他神情安详,笔挺地坐在座位上,身体没有半点歪斜……”
“这张照片,震撼了我的心。我能够想象,发病的时候他有多痛苦,却无法想象他如何能够坚持下来,如何能够不发出半点声音,如何能够在生命的最后一秒还保持着军人的姿态?”
“我想,他的一生就像带着学生去攀登,走过千山万岭,眼看要登顶了,却突然倒下。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拼劲全身力气,把学生高高举过头顶!”
“导师在世时,我们觉得他可亲;导师走了,我们才感到震撼。”学生商景龙,尽管对导师一家非常熟悉,但严高鸿去世后,当他来到严高鸿家里祭奠恩师时,师母王建清的一番哭诉,竟然让他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