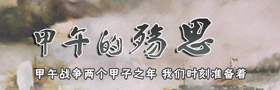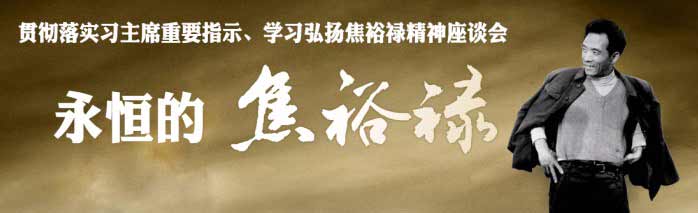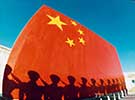“那天,师母边哭边讲我们那一届学生论文开题前夕在导师家讨论研究的情景。随后,师母讲起当时我们每个人的表现、我们写论文时遇到的困难,导师是怎样评点的,以及我们各自对论文是怎样修改的……”
“我顿时惊呆了,腮边的泪也忘了擦。师母是一名普通职工啊,绝对不是学哲学的,何以能够如此专业地说出我们当时都感到十分困难的哲学问题?何以在时隔四五年之后,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出当年的细节?”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老师生前一定反反复复跟师母说起我们这些学生。有不少同志,下班就像关电灯一样,把工作也‘关’掉了,回家就是休息、娱乐、处理生活问题。可是,导师上班想的是学生、下班跟师母念叨的还是学生,而且说得那么多、那么细。他就像一个磁场,把师母也磁化了!”
■“导师的学生未必都有学籍,视他为恩师的,何止三千桃李”
严高鸿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对远道而来的夫妇痛哭不已:“严老师,我们会一辈子记得你跟我们说的话!”
当时,严高鸿的很多学生在场,大家谁也不认识这对夫妇。可以肯定,他们并非出自师门。那么,严高鸿生前对他们说了什么话,让他们终身难忘?
这,至今仍是严高鸿学生们心中的一个谜。但是,学生们这样说:“导师的学生未必都有学籍,视他为恩师的,何止三千桃李!”
有谁能想到,严高鸿的“学生”中,居然有一个小老板!
一年春节,严高鸿回家乡安徽省广德县探亲,小煤窑老板宁其斌问:“我想再办个造纸厂,你看怎么样?”严高鸿说:“为什么不在竹子上想出路呢?我们广德是全国著名的竹乡啊!”宁其斌笑了:“加工竹子能挣几个钱啊?”严高鸿耐心解释:“国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小造纸厂污染大,是严控行业。搞竹制品深加工就不同了,这是绿色经济、环保企业,很有发展前景。”
宁其斌半信半疑,办了一家生产竹制地板的公司。后来,这家公司在技术上遇到难题,严高鸿又亲自跑到南京林业大学,为宁其斌引进新技术牵线搭桥。如今,这家企业年产值已上亿元,产品远销海外。
回首往事,宁其斌最感谢的人就是严高鸿:“没有他老人家的点拨和帮助,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说他是我创业的导师,一点不过分!”
学报编辑周峰,也并非严高鸿的亲传弟子。2009年12月,他硕士研究生即将毕业,却拿不出几篇像样的学术文章,心里很着急。考虑到严主编定下过“编辑部内部人员稿件一律不照顾”的老规矩,他试着把一篇论文寄给了另一家杂志。
两天后,那家杂志来消息了:此稿可用,但要交1500元的“版面费”。周峰去找严高鸿商量,严高鸿严肃地说:“小周啊,这样的文章就是发出来了又有什么意义呢?你是当学报编辑的,要是迎合了这样的不正之风,今后还怎么能发自内心地公正处理作者的稿件?要对别人负责,先要对自己负责呀!”
“这番话,好像在我背上猛击一掌!回去以后,我马上回绝了那家杂志。虽然文章没有发出来,但我心里却踏实了很多。”回忆往事,周峰对记者说:“严老师对我立身做人的帮助最大,他是我人生的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