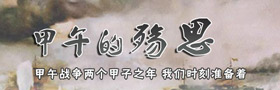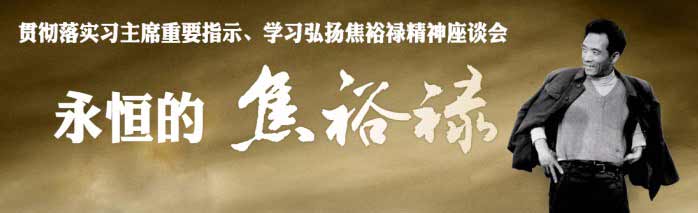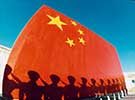第五章 /长葛探索
一、探索“户包总产”
长葛调研期间,习仲勋还指导了“户包总产”的探索与实践。
包工到户、定田到户、包产单位越小越好等“包产到户”方法,一直都不同程度地在大跃进的夹缝中生存着,它是中国农民自发寻找自救之路的方式或方法。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影响下,包产到户成为被批判、被打击的对象。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习仲勋指示“户包总产”、“不要向外宣传扩散”。这段鲜活的历史,时至今日还鲜为人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习仲勋心情沉重地发现:农村出现大饥荒,很大程度上在于农村政策和工作方法不对路,最根本的是按劳分配出了大问题。社员一个工分折合8厘钱,一天做10个工分才8分钱。一个强壮男劳力干一天活,还不如一只母鸡下一个蛋值的钱多。大家对种地不感兴趣,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往城里跑,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习仲勋提出,要成立一个“经营管理调研小组”,由时任长葛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任组长,时任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宋德明与和尚桥公社党委书记孔宪瑞为副组长。同时,抽调董欣亭、苏林堂、朱保安、苏明瑞、周洪信等8人组成调研小组,进行联产承包试验。
习仲勋在县委前的大桐树下,对这些参与试验的干部说:你们不要怕这怕那,我们知道,搞公社经营也好,搞小队经营也罢,都不可能照着现有的那一套办法去描去画了。老百姓生活现在那么困苦,解放10多年了,农村还是破破烂烂。眼下缺粮又缺菜,照老办法去描,能解决问题吗?只要对生产有利,什么办法都可以试。老百姓多打粮食了,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好处,何怕之有?搞对了,是大家的;搞错了,我们和县委负责。
在习仲勋的安排下,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定点在桥北、胥庄村搞试点。记工评分,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分配形式。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对5种记工评分办法进行试验,看群众对它的反应与生命力。
结果,5种办法,都以失败而告终。
譬如,试用“劳动定额管理办法”,即把所有工种活,以一个中等劳动技能、诚实劳动态度、适度的劳动工具,按规定的劳动时间、一般农活质量标准,制定出不同工种项目的劳动定额,各个劳动者干什么活,记什么工种的工分,就像查字典一样对号入座记分。试验发现,这个方法听起来一劳永逸,简便易行,可做起来,就出现了干活不讲质量,地头路边做得好,中间草上飞,“张冠李戴”,定额高的争着干,尤其是雨天、难活、脏活没人干。加上劳动计时无凭证,难以准确地判断出各个劳动者所报定额的对和错、高或低。
这个法不行,再试用“基本劳动日制度”,解决劳动均衡的问题。试用后发现,这样做了,虽然省去了记工评分时等诸多问题,生产队干部只负责查验农活质量就可以了,劳动者会经常主动找活、要活干。但还是出现了天气好、气候好、温度适宜时出工的多,反之,出工的少。
如此不厌其烦地在过程上下工夫,不在终极产品上做文章,只能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5种试验相继失败。
那时候,国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队为基础”基本国策,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再往下分,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而当时的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连社员名字都写不全的人”,管理着成百上千的劳动者。如此这般,只得沿用打钟集合、站队等活、一窝蜂,背工窝工现象非常普遍。
这样,建立作业组、划分耕作区一时成为群众的呼声。习仲勋顺应民意,鼓励经营管理调研小组大胆探索。
建立作业区、划分耕作区后,农、工、商、牧、副、杂各业,由谁经营、谁管护耕作,清清楚楚摆在那里,谁勤快、谁懒散,谁下工夫,付出的多,明明白白地体现在各种作物上。这样的话,实行联产承包,就成了广大社员的一致要求。
各家各户如何联?干部们提出了多种办法。最后,百分之八九十的社员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联产承包到户包总产。一年一算,一包到底,缴够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如果这样,干得好了吃蒸馍,干不好了吃窝窝,谁也怨不得谁。劳动积极性不用干部催促,就自然而然地调动起来了。
习仲勋敲定:可以试验。
来自群众的办法一经公布实施,想不到的优越性立马就体现出来了。社员们积极攒肥,主动学习农业技术,没日没夜地干活。
习仲勋在向邓小平和中央写的第二份《关于长葛农村的调查报告》中说:“干部群众对包总产的办法特别拥护,就是因为一包总产,生产队就真正当家做主了,生产队才真正有权因地制宜,合理地种植各种作物,从根本上杜绝生产上的瞎指挥。”
尽管习仲勋离开了长葛,但是,他指导下的联产承包“户包总产”经过一年实践,有了结果:试验的两个村当年公余粮一斤不欠地完成了,集体的提取一元不少地提够了。116户社员,户户增产增收,家家有余粮。
当时谁都没有料到,这种联产承包“户包总产”形式,到20世纪70年代经安徽小岗村农民再创造,发展完备而为“单干风”吹遍全国,成了国家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