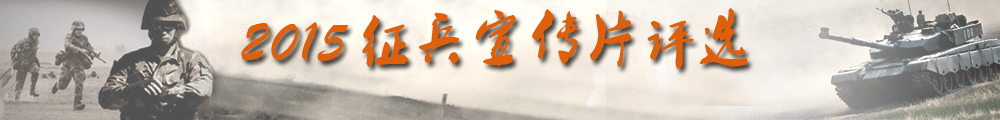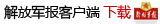我入伍任战士期间,当过好几年雷达部队的汽车兵。雷达部队下设的雷达站地处分散,大都设在边界线上。而从团部出发到最边远的雷达站相距有一千多公里之远,几乎要横穿整个内蒙古大草原。雷达站的供给和器材更新,都要靠我们汽车连的运输完成。一年四季,我们频繁地深入草原,奔驰往来。
我第一次跑长途,是在当兵后第二年的一个冬天。同行的老兵姓刘,是山东人。他已经在草原上跑过不知多少次了。他是带车的老兵,见多识广。刘老兵有个习惯就是在车上吸烟。车一上路,他便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烟是自卷的,用报纸裁成有规则的纸条包起来,整齐又厚重地揣在上衣口袋里,鼓鼓的。起初我还以为兜里装的是人民币呢。刘老兵抽的是旱烟,味道又臭又辣,熏得人睁不开眼睛。因为烟是自己卷制的,只用唾沫蘸了一下,所以那烟会边吸边跑气漏风。刘老兵每次吸烟都拼命地一口口地去嘬那烟的一端,烟头烧得吱吱响。整个驾驶室里都是臭烘烘的。
老兵吸足了烟,身子便往副驾的座椅上一偎闭上了眼睛。这是我第一次跑长途,见刘老兵闭上了眼睛,心里就有些慌。我就喊他:“刘班长,你别睡呀,我怕开错了路。”那时我们新兵把所有的老兵都叫班长,以示尊重。
刘老兵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用肘往前一比划道:“顺着道往前开,别拐弯。”有了他的指示,我就沿着马路一直往西开了。
部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配备的军车,都是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里装满了雷达站所需的生活用品和雷达器材,货物被一块军绿色的苫布蒙上了。草原风大,苫布掀起一角,在风中呼呼啦啦地一路响着。老解放车门关不严,总有硬硬的风吹进来,冻得我的手脚一阵阵发麻。于是我便用右脚踩油门,左脚不停地在驾驶室地上跺来跺去。刘老兵听到声音掀开一道眼缝,眯了我一眼,鼻子里哼了一声,便又侧过身养精神去了。我加大油门,让车号叫着向前奔去。
快到傍晚时,前面没路了,只剩一片茫茫的雪原。路边有几株顽强的蒿草从雪地里探出头来,在风中一起一伏。我把车停下来,叫醒刘老兵。他看了一眼雪原,又看了看外面的天气,把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出一张烟纸,又从另外一个衣兜里拿出一些细烟末,然后卷起烟来吸。刘老兵一连吸了两支,才指了指地上,冲我说:“你下车。”
我下了车,走到副驾驶门口,刘老兵直接从副驾坐到正驾位置上。我这才上车。一上去,刘老兵就一脚油门让车蹿到了雪原上。我已经开了大半天车了,夜路该刘老兵开了。这是我们事前说好的。刘老兵不放心我开夜路,更不放心我在黑天的雪地上跑长途。
天转眼就黑了。只有车灯照着前面的一点路程。前方的路无论怎么看,都不过只是毫无变化的雪路。偶尔可以看见别的车留下的模糊痕迹。风刮在雪上,迷迷蒙蒙一片,看久了,会觉得方向都辨认不清了。我坐在车里早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而这一千多公里,我们要不停歇地跑,因为中间没有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也只能赶夜路。我看了一眼刘老兵,他的一双眼睛直视前方,就像指南针一样,一会儿开向左,一会儿开向右,但神奇的是我们的车始终没有偏离模糊不清的雪路,我心里暗想,毕竟是老手啊。
刘老兵发现我在看他,瓮声瓮气地说了句:“你眯会,有事我叫你!”说完便不再说话,继续认真地开车。脏乎乎的手套下面的方向盘被他拧得吱吱响。我听从了刘老兵的建议,歪在椅子上休息。单调的雪路也让我的眼皮发沉,不知不觉就迷糊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我感觉到车似乎停了下来。我睁开了眼睛。
刘老兵在旁边骂了一句:“妈的,车开锅了!”
我抬头一看,果然车头上冒出了一阵白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