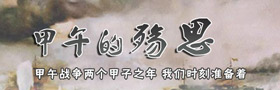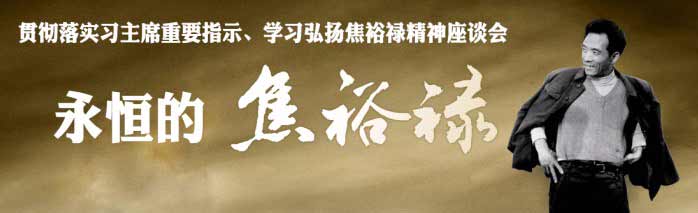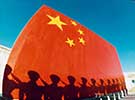夜行,死里逃生
她用左手压住胸口,刚才的一幕越想越后怕,如果再晚回头一秒钟,那人的匕首就会刺进她的后背,或者她正好回头时刺进她的喉咙……
2004年,王伟成为中国首批赴科索沃执行任务的维和警察中的一员。
在科索沃维和任务区,联合国车辆是统一分配的。每个部门负责人会根据工作人员和车辆的数量分配几个同事合用一辆车。惯例是,拿到车的人需要每天把同车的几名同事送回住处,早上再接这几个人共同上班,一是为节省资源,同时也是安全需要。
王伟主动声明,没有特殊情况不用接送她。一来警察总局离她的住处并不远,步行不到20分钟;二来,她住的居民楼周围停车很不方便,车子停在临街小道上更不安全。
可是,好想法差点酿成大悲剧。
一天晚上8点多,忙完手头的工作后,王伟习惯性地查查邮箱,回复了几封工作函和私人邮件,然后便站在窗边,凝视着满天星辰,让整天对着电脑的眼睛放松一下。忽然,窗外传来了乌鸦一阵阵“嘎嘎”的叫声,叫得她心里发慌,脊背顿时冷飕飕的。在国内,按照老人的说法,乌鸦在头上叫可是不祥的预兆。但自到科索沃以来,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都可以听到乌鸦的叫声。不管走到哪里,大片大片的乌鸦满天飞。据当地人讲,“科索沃”这个地名的原意就是乌鸦聚集的地方,无数乌鸦都是循着腐败尸体的味道而来。讨厌的乌鸦叫打破了王伟心里的宁静,她把手伸出窗外试了一下,天空中已经下起毛毛细雨。王伟披上警用雨衣,准备返回住处。
返回住处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垃圾场,原来是田地,后来被北约的炸弹炸出了几个大坑,任务区的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都扔在那几个炸弹坑里。这里时常会有大量野狗光顾,北约部队曾组织过两次集中清除野狗的行动,可还是无法将这些找食吃的野狗赶尽杀绝。这些野狗以死尸为食,也袭击活人。
就在这天晚上,王伟路过那个垃圾场时突然被十几条野狗“呼”地一下围住。王伟一下子蒙了,停在中间一动也不敢动。以前王伟也遇到过被野狗围攻的状况,可那是白天,而且是和当地警察一起。当地警察告诉她,这些野狗对枪和枪声特别敏感,遇到野狗只要伸手摸枪,它们就会立刻散开跑掉。
这一招王伟试过,一直挺灵的。可此时是晚上,野狗看不见她摸枪的动作,它们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幽幽的绿光,如饿鬼般冲她不停狂叫……
王伟不敢喊,她怕喊声会刺激野狗,适得其反。她心里明白,只要有一只野狗率先进攻,其他野狗就会群起而攻之。一旦自己被扑倒,那可就彻底完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王伟的手摸到了武装带上的手电筒,顺势掏出来向后扔去。野狗一见有了新的“猎物”,呼啦一下,一窝蜂地狂叫着追了过去。
王伟撒腿就跑,直到确定安全了才刹住脚。她气喘吁吁,心狂跳不止:这要是让野狗给吃了,也死得太窝囊了。
然而,王伟的厄运还没结束。
接下来的这段路算是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的繁华路段,一溜有几间酒吧,一到晚上就会传出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声。走到这里,王伟不用再担心被野狗追了。她的心情放松下来,随着音乐的节奏,伴着几盏昏暗的路灯往住处走去。
正要拐进小道时,王伟突然发现前面路口站着一个人,向她这边快速瞥了一眼,转身消失在黑暗中。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立刻引起了王伟的警觉。
王伟放慢脚步观察四周,没发现什么不对劲。经过下一个路口时,她下意识地左右张望了一下,依旧没发现任何人。心里还纳闷呢,这才不到9点,往常这时候街上还能看见行人,今天怎么这么静呀,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都到哪儿去了?
这时,王伟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
难道是幻觉吗?王伟稍稍偏了一下头,用余光一扫——没错!真的有人跟踪!
王伟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可是她走得快,后面的人也快,她慢下来,后面的人也慢下来。冷汗从王伟后背流下来,怎么办?
身后男人的喘息声越来越近,王伟猛地转身——一个手持匕首的男人已经扑到了跟前,距离她只有一两米了!
接下来那一瞬间王伟的反应,成了这位冰城女警维和生涯中最传奇的一幕。王伟一气呵成地完成了那一套动作——拔枪、开保险、上膛、瞄准,同时怒喝: “What are you doing(你想干什么)?”
昏暗寂静的大街上,王伟的吼声显得格外尖厉。那家伙一下子愣住了,举着刀的手悬在空中,整个人似乎被钉在了地面上,满脸的惊讶和疑惑。他大概弄不清楚,刚才那震慑人心的声音怎么会出自眼前这个柔弱的东方女孩。
两人静静对峙了数秒钟,男人的眼中闪过一丝恐惧——王伟知道,他已经清楚地看见了对准他的黑洞洞的枪口。
“What are you doing ?”王伟再次喝问。
“当啷”一声,那家伙手中的刀掉在地上,连连后退,嘴里叽里咕噜,意思大概说这是个误会。
王伟死死盯着他,双手举枪的姿势依旧保持着,食指搭在扳机上,脑子里却像念咒似的反复权衡:开枪?不开枪?
男人大概认为面前这个小姑娘的枪口随时会喷出火光,三十六计走为上,转瞬间,他消失在黑暗中。王伟没有追,也根本不打算追。虽然联合国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开枪,但事后的报告程序相当复杂。再说,对方自从扔掉了匕首,就只能算手无寸铁的平民了,而她是维和警察。就算他真的要抢她,她也不忍把对方置于死地,毕竟在科索沃的特定环境下,抢劫者也多是为生活所迫。在任务区能不动枪就尽量不动枪,这是原则。王伟不想成为因个人安全在科索沃放第一枪的中国维和警察,也不希望任何一个因为生活所迫而抢劫的家伙成为她的枪下之鬼。
王伟僵硬地站在刚刚发生过“生死搏斗”的现场,看到了那家伙掉在地上的匕首,她的手抖得厉害。雨一直在下,王伟的雨帽早已被风刮掉,雨水浇湿了头发。过了很久,她才把枪放回枪套,轻轻嘘了口气,低声自语:“好险……”
回到住处,关好门,王伟顺手把门钥匙插在钥匙眼儿里——这是王伟在科索沃的一贯做法,这样就会防止有人撬锁,不过主要是为了给自己壮胆儿。她用左手压住胸口,刚才的一幕越想越后怕,如果再晚回头一秒钟,那人的匕首就会刺进她的后背,或者她正好回头时刺进她的喉咙……
第二天,王伟一上班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把她的遭遇报告给行动部信息中心,提醒维和人员夜晚出行时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二件事是到枪支管理处领来枪油,把枪拆开,彻底地擦拭了一遍。她要好好爱护枪,是它救了自己。
此刻,王伟内心对“鹰巢”的张教练充满了感激。
希望,在眼泪中绽放
有听说联合国招聘阿语和英语翻译,百撒终于找到了希望,决心把上学时学的英语捡起来,拼一把。于是,她白天一边跪在街上乞讨,一边学英语……
身处动荡的异国他乡,才深切体会到和平的可贵。
科索沃人口约200万——和我们国家公安民警的总数差不多,面积10887平方公里,境内河流众多,土地肥沃,按说这样的人口和土地资源比例是很适宜人类生活的,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
王伟在科索沃工作期间,奉命组织了一次特殊的考试,为当地警察局招录20名勤杂工,这让她对科索沃当地的现实生活状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有一个叫吉拉米的妇女,面试时给王伟讲述了令人痛心的家史。她虽然面带笑容,眉宇间却流露出隐隐的哀伤。
“你家几口人?”王伟问。
“就我和儿子,儿子10岁了。”她干脆利索地回答。
“就你和儿子?”王伟有些奇怪。大多数求职者都是拖家带口的,一般都是五口以上,十口以上的也不在少数,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甚至五代同堂,仅有两个人的家庭不太常见。出于好奇,王伟和吉拉米多聊了几句。
没过多久,王伟就泣不成声了。
战争发生前,吉拉米和丈夫在喀达查尼查有一片菜地。白天吉拉米在家里打理家务,照顾孩子,丈夫就到集市上去卖菜。这是个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式家庭,让全村的人很是羡慕。没想这该死的战争毁了她的家。周围的邻居都急着逃往邻国去避难,她就劝丈夫也快逃,可丈夫说什么也不走,说这正是丰收的季节,越是战乱蔬菜越能卖个好价钱。她丈夫一向很倔,还说:“谁没事儿会把炸弹扔到咱家这个破菜园子里?”
没想到有一天,丈夫正在菜地里干活儿,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自天而降,就在她家菜地旁边炸开了。炸起来的土块砸在她丈夫的头上,他当时就昏了过去,连震带砸,丈夫的大脑神经受到损伤,从此变得痴痴傻傻的。吉拉米的生活一夜间全变了,用她的话说:“真像做了一场噩梦。”
一天,吉拉米不在家,傻丈夫丢下孩子,光着脚跑了出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直到数月后,北约士兵在一次搜索行动中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到现在她都不知道丈夫是怎么死的。
吉拉米边哭边抹泪,把为了能给面试考官留下好印象特意涂抹的睫毛膏和粉底抹了一脸花。她说她好几次都想一死了之,可就是放不下可怜的儿子。孩子太小,而她的许多亲属都在战争中死去,这可怜的孩子连个寄养的地方都没有。现在,只有她和儿子相依为命了。
吉拉米一家的悲惨遭遇让王伟难过至极,就是那么一颗莫名其妙飞来的炸弹,让原本一个美好的家庭刹那间化为乌有,彻底夺走了吉拉米一家的希望和未来。而且,还要让活着的人继续遭受情感的摧残和肉体的折磨,这也太残忍了,这也太不人道了。
于是,王伟在她的名字下面画了一个对钩。这个对钩,对吉拉米而言,就是拉了她一把。
参加面试的人中相当一部分是男人。生活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放下男子汉的架子,即便是“女人干的活”,他们也要争取。
“请问你们想得到这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女人干的活你们能干吗?”王伟问。
“还有一大家子人需要养活。”男人们的回答惊人地相似。
有一个壮小伙跟王伟说,家里有九口人等着他养活,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两个妹妹,还有妻子和女儿,全家只有他能找到事做,他一个人在支撑着一个集体失业的大家庭。他说他现在同时打三份工,每天工作16个小时,这份勤杂工作不算太累,还能多挣点钱贴补家用。他太需要钱了!
“这样下去你撑得住吗?”说句心里话,王伟打心眼里想给他这份工作,可又担心他这样拼命下去,一旦累倒,这个九口之家将会怎样?
“再苦再累我也得撑着,直到我爬不起来那天为止。”小伙子嗓音低沉。
王伟的心里一阵酸痛,恻隐之心的驱使让她给他打了个最高分,希望能帮助他得到这份工作。可王伟知道,类似的家庭又何止一个!
说起不幸,还有王伟的女翻译百撒。
百撒又瘦又高,齐耳短发,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女性。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她的眼眶凹陷进去,黑黑的眼圈把她的年龄放大了四五岁。
闲暇时,王伟和她坐在楼下的咖啡馆里聊天,她面前放一盒烟,一口一口吸着,再吐出一团一团的烟雾,似乎想让那苦难的过去被烟雾淹没。
百撒是个孤儿,父母早年去世,扔下她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为了生存,她什么活都得干。
战前,百撒在一家面包店做事。为了多挣点钱,她总是加班,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老板看她能吃苦,人又诚恳,体谅她的难处,每次到发薪水的时候,就会偷偷多塞给她一个红包。可是,一颗可恶的炸弹把面包店炸得粉碎,幸好那天她没有上班,算是捡了一条命。
没了工作,一日三餐很快变成了一餐,到后来,连这一餐也都无法保证了。她不能眼看弟弟妹妹在家饿死,于是带着弟弟妹妹投奔联合国难民署临时搭建的难民营。为了能让弟弟妹妹比别人多吃上一口,她走上街头乞讨。换位思考一下,一个漂亮的女孩跪在地上,乞求路人的施舍,期待着哪位好心人把硬币扔在她面前的盒子里,她的心里是在滴泪还是在滴血?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多。有一天,听说联合国招聘阿语和英语翻译,百撒终于找到了希望,决心把上学时学的英语捡起来,拼一把。于是,她白天一边跪在街上乞讨,一边学英语……
说到这里,百撒不停地吸烟,又不停摇头,眼睛湿润了。那是她最痛苦、最屈辱的时刻。王伟猜想,跪在地上边乞讨边背英语的百撒当时一定在想:“终于有一天,我会挺胸抬头地站起来的!”如果真有一天,百撒佝偻的身躯自豪而骄傲地挺拔起来,亭亭玉立站在人前,她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会为全天下爱说、爱笑、爱美的女人书写一部自强不息的神话。
百撒最终如愿以偿了,她熟练地运用英语翻译阿尔巴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成为任务区的急缺人才,再也不用担心过以前那样的生活了。她用坚强的意志书写着她自己的人生,她成功了。
百撒讲述自己的经历时,表情很平静,没有王伟想象中的“往事不堪回首”,她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百撒,少抽点儿吧!对身体不好。”王伟劝她。
“咳!已经上瘾了,扔不掉的。”她苦笑着回答。
王伟知道,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她的精神麻醉剂了。其实,百撒并不是扔不掉烟,而是扔不掉那痛苦的记忆。
王伟静静地听着,不想问得太多,她怕自己的好奇心触痛百撒的自尊心。王伟知道,有自尊就有希望。伤痛让她自强不息,伤痛让她坚强挺立。她们才是希望,是科索沃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