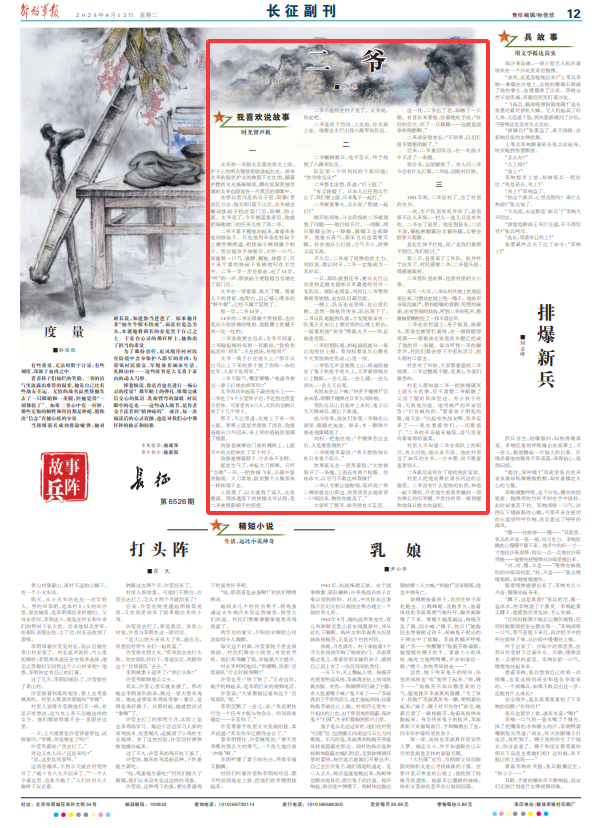二 爷
■邹 冰

一
太爷将一页耐火瓦盖在炭火上面,炉子上的明火慢悠悠收敛起红光。原本太爷的脸在炉火的映照下红红的,随着炉膛的火光渐渐暗淡,蹲在窑洞里抽旱烟的太爷也隐没在一片黑沉的烟雾中。
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阳婆(晋语区方言,指太阳)落下山后,太爷就会搬动铁砧子挡在窑门后,防贼、防土匪。太爷老了,今年割罢黍麦后,他就把每晚堵门的任务交给了我二爷。
二爷不紧不慢地站起来,拿着布条走向铁砧子。只见他用布条在铁砧子上横竖绑两道,把铁砧子绑得像个粽子。然后他双手伸展开,大呼一口气,再猛吸一口气,猫腰、撅腚、伸脖子,百十来斤重的铁砧子竟被他叼在半空中。二爷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了14步,“咚”的一声,那铁砧子便稳稳当当堵在了窑门后。
太爷在一旁看着,张大了嘴。看着儿子的背影,他明白,自己精心喂养的“野牛犊”,已经不属于窑院了。
那一年,二爷14岁。
14岁的二爷长得像个黑铁塔,也许是从小抡铁锤的缘故,他胳膊上的腱子肉一坨一坨的。
二爷说他要去当兵,太爷不同意。二爷瞪起铜铃似的一双眼说:“您给我起名叫‘将军’,不去战场,有啥用?”
太爷一筷子打在他头上:“那年从白马山上下来的那个救了你妈一命的红军,人家才是将军。”
二爷不服气,嘴里嘟囔:“难道我要当一辈子打铁的将军吗?”
太爷再次举起筷子敲在他头上——二爷吃了9个玉茭饼子后,手还想往笸篮子里伸。可家里有4口人,太奶奶后晌只烙了十几个饼子。
那天,天已黑透,北坡上下来一伙土匪。那帮土匪显然得到了消息,狗蛋爸刚从口外回来,身上背的褡裢里装满了银圆。
狗蛋爸被绑在门前的槐树上,土匪手中的火把映红了半个村子。
狗蛋爸梗着脖子,宁舍命不舍财。
匪首生气了,举起大刀挥舞。只听“当啷”一声,一把铁锤飞来,正砸中匪首脑袋。大刀落地,匪首整个人像面条一样软塌下去。
土匪慌了,以为遇到了高人,仓皇撤离。现场遗落下的铁锤太爷认得,是二爷使得最顺手的那把。
二爷不能待在村子里了。太爷说,你走吧。
二爷连夜下西沟,上北沟,往北原上走。他要去太行山找八路军的队伍。
二
二爷辗转数日,吃尽苦头,终于找到了八路军队伍。
队伍里一个叫刘权的干部问他:“你为啥当兵?”
二爷想也没想,答道:“打土匪。”
“有点狭隘了。日本人已经到太行山了,我们要土匪、日本鬼子一起打。”
二爷握紧拳头,点头说:“那就一起打!”
刚开始训练,斗志昂扬的二爷就遇到了问题——他打枪不行。一闭眼,两只眼睛全闭;一睁眼,眼睛又全部睁开。他垂头丧气,原来当兵也需要天赋。好在他从小打铁,力气不小,投弹又远又准。
不久后,二爷成了投弹组的主力。刘权说,假以时日,二爷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兵。
一日,部队接到任务,要从太行山谷里抄近路支援和日军遭遇的另外一支队伍。部队走得急,刘权让二爷帮炊事班背铁锅,走在队伍最后面。
一晚上,队伍走走停停,在山里打转。忽然一阵枪声传来,队伍停下了。二爷从队尾跑到队前,才发现原来有一队鬼子正在山上朝对面的山坡上射击,一挺重机枪“突突”喷着火舌——队伍前进受阻。
二爷回到队尾,抄起扁担就从一条山沟里往上摸。等刘权看见半山腰有个大黑铁锅在晃动,心里一惊。
二爷悄无声息地爬上山,将扁担抽在了鬼子机枪手的头上,又背着铁锅在山上跳跃,一会儿高,一会儿矮,一会儿消失,一会儿又出现。
有战友在山下喊:“快丢手榴弹!”话音未落,两颗手榴弹在日军头顶炸响。
等队伍从山后面冲上来时,鬼子以为天降神兵,朝山下溃逃。
战斗结束,战友们发现二爷躲在山洞里,眼睛在流血。原来,有一颗弹片崩进他眼睛里了。
刘权一把抱住他:“手榴弹丢出去后,人是要卧倒的!”
二爷嘻嘻笑着说:“我不想给狗日的日本鬼子低头。”
炊事班长在一旁黑着脸,“大铁锅裂开了一条缝,上面还有两个枪眼。你娃命大,以后可不敢这样莽撞!”
二爷以为要让他赔锅,低声说:“我二姨家就在山那边,我黑夜里去她家背一口锅回来,赔给你就是了。”
大家听了都笑,却笑得有点苦涩。
这一仗,二爷出了名,却瞎了一只眼。有首长来看他,拉着他的手说:“好好的后生,坏了一只眼睛……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啊。”
二爷却安慰首长:“不妨事,以后打枪不需要闭眼了。”
后来,二爷重回队伍,在一次战斗中又没了一条腿。
再后来,全国解放了。有人问二爷今后有什么打算,二爷说,回乾村打铁。
三
1951年秋,二爷回村了,当了村里的支书。
一次,生产队里的机井坏了,县里派不出人来修,一村人一连几日没有水吃。二爷去了县里。他见到县长,二话不说,撩起裤腿露出半截伤腿,又要去抠那只假眼。
县长忙伸手拦他,说:“是我们做得不到位,我们检讨。”
第二天,县里来了工作队。机井终于出水了,村民感谢二爷,二爷摇头说,得感谢政府。
二爷管队里的事,也管村里的大小事。
每天一大早,二爷从村外坡上的地窑里出来,习惯站在坡上吼一嗓子。他的声音低沉威严,那些聒噪的喜鹊、叽喳的麻雀,还有哭闹的娃娃,听到二爷的吼声,都像被浆糊粘住了一样不再出声。
二爷走在村道上,身子挺直,扬着头,那条空裤管打着结,在一根拐棍旁晃荡——那根油光发亮的木棍已经成了他的另一条腿。每当听到二爷的脚步声,村民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计,扭头朝村口望去。
村里有了纠纷,大家都愿意找二爷说理。二爷话糙理不糙,是真心为他们着想的。
村里人都知道二爷一把铁锤砸死土匪头头的事,但不清楚二爷眼瞎了又没了腿的具体经过。有小孩子好奇,天真地问他。他用威严的声音回答:“打仗被炸的。”看着孩子明亮的眼,他又说:“比起有些战友啊,我幸运多了……现在看着你们,一切都值了。”二爷的声音越来越低,语气里竟有着难得的温柔。
村里人不知道二爷在部队上的职位,有人问他,他从来不说。他在村里当了20年的支书,一生未娶,说不愿意连累别人。
二爷最后老死在了他的铁匠窑里。
村里人把他安葬在漠谷河边的公墓里。二爷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和他一起下葬的,只有他生前喜欢戴的一顶有弹孔的旧军帽、平常拄的那一根拐棍和他每日挑水的扁担。
本版插图:赵建华
图片制作:陈新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