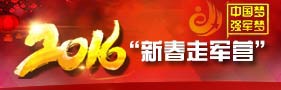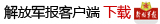“刘大哥”是最可爱的朋友
也许是因为我的名字有些男性化,所以很多未谋过面的读者以为我是男性,没想到还带来一些便利。当时报社领导考虑我学过医,让我开办了一个《军营卫生》专版。专版创刊后注重服务和贴近青年官兵,引起了读者关注。特别是有些官兵遇到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问题时,常常把《军营卫生》的责任编辑当作知己,写信倾诉他们的烦恼和痛苦,信的排头称“刘大哥”。
在接到这些来信后,我便将错就错,以男性的身份与他们沟通。记得有一个干事来信倾诉他遇到的关于隐私方面的烦恼,痛苦万分。我便长时间和他通信,帮助他勇敢地战胜心理疾患,使他走出痛苦的梦魇。当他终于站在灿烂的阳光下,幸福地拥抱新的生活时,他写信说:“刘大哥,你是我最可爱的朋友。”
女记者“五同”变“四同”
作为女军事记者,我每年不落地要参加“记者蹲连”活动。第一次“记者蹲连”,领导居然没有把我排列在名单内。我去找领导,领导说,其他“四同”还可以,你怎么同战士住在班里?我说,我可以住在招待所,或者女兵连。领导看我“请战”坚决,非去不可,便批准了,此后历次“记者蹲连”,领导似乎不再考虑我是女记者,排列名单必是第一批。
我曾经多次到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采访,6次跟随这个旅拉动,3次参加这个旅的实弹发射,5次随旅队千里机动参加重大演习,这个旅从组建到不断壮大,走过了曲折而辉煌的历程。在他们艰苦跋涉的20多年时间里,我一次又一次目睹了火箭军磨砺长剑的壮举,在和官兵一起把巨龙隆隆开进、把导弹送上蓝天时,我采写了见证新一代火箭军成长的系列报道。
有一年,我奉命又一次参加“记者蹲连”活动,来到该旅二营三连——军委命名的“导弹发射先锋连”参加军事演习。连队每天日落而动,日出而息,官兵披一身夜幕,试长剑锋芒。当时正值南方的雨季,烟雨蒙蒙,铁流滚滚,我身着迷彩服,每天晚上随队采访,白天伏案写作,在帐篷里和官兵交流,在连队里吃野炊饭菜,即使臂膀和腿脚被蚊子叮得鲜血淋淋也乐此不疲,深入调查并采写了《8000篇训练日记研究失败》的消息,获得解放军新闻奖。
军人战斗岂止在战场,当我在导弹阵地采访,抚摸着那些“庞然大物”时,官兵对我说,存在就是威慑,备战就是打赢。当我和官兵拥抱在一起,庆贺导弹发射成功时,我知道了“战略”二字的分量。我置身官兵行列中,真正明白了和平时期的军人事实上是在看不见的硝烟中打仗,是在用实力迎接战争、遏制战争。